在知乎有一个提问“关于死亡你有什么想说的,想分享的?”
蔡澜先生的回答中提道:骨灰撒在维多利亚海港,每晚看到灿烂的夜景,更是妙不可言,你说是吗?
这不是文人矫情的浪漫,而是蔡澜先生发自内心的潇洒。

曾经坊间流传一件轶事:一次夜间坐飞机,因为突遇气流飞机颠簸不止,蔡澜先生身旁的人拼命抓住扶手,而他却一口一口不断地灌酒。飞过气流后,那人恐惧疑惑地问:“老兄,你死过吗?”而蔡澜放下手中的酒杯,一脸满不在乎地回:“我活过。”

大有三国中诸葛亮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畅快,生命永远不该用来担惊受怕,而是应该活得有趣。
同为香港四大才子的金庸先生曾评价他: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他不弹古琴、不下围棋、不作画、不嫖、不赌,但人生中各种玩意儿都懂其门道,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说是第一流通达。

蔡澜先生头顶作家、电影制片人、美食家、旅行家等一连串的高帽,丝毫不觉得脖子僵得慌,他所得到的都只是他想去做的,只不过因为他本身的执着和横溢的才华让他在每条路上都走的很远,可是他只会对着镜头微微一笑,“怎么叫都好,我都很感谢。不过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一生做错了一件花四十年才知道是错的事,不应该一直沉迷在电影行业里面。”

蔡澜先生一直是库布里克忠实的粉丝,所以在18岁那年选择赴日本就读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因为父亲蔡文玄和邵逸夫兄弟一起做生意,负责邵氏电影在东南亚的院线电影安排,所以蔡澜很容易搭上了邵氏公司这条线。
就读期间他成为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六年后,蔡澜定居香港,担任起嘉禾电影的制片经理。
他任职期间,曾制作了一系列成龙电影,例如《龙兄虎弟》、《福星高照》、《重案组》等等,可随着工作战线的拉长,他越加的迷茫。

这就是我一直坚持的电影梦?
这是我的电影噩梦吧!蔡澜苦笑一下,他深知电影行业也是一门生意,而他想追求的却是艺术,他曾像邵逸夫提出建议:一年拍四十部电影,何不拍三十九部卖座电影,一部用来追求艺术?
但一个生意人为什么要“为了艺术为了理想”呢?
这是个莫比乌斯环,即便让牛顿过来也无解。
改变是需要无比巨大的勇气的,尤其是随着岁月拍打,很多人都只会变成王小波笔下被捶打驯服的牛,但是蔡澜先生却在不惑之年毅然决然地回归到写作路上。
为什么说是回归呢?
在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蔡澜写下第一篇小说《疯人院》发表到新加坡《星洲日报》上,拿着稿费请一帮子朋友胡吃海喝一顿,那都是三十年前的事啦。
他从未想过有一日,自己会成为在30年写下200本书的大作家。

蔡澜先生文字精简隽永,有一股子气在其中。
这股气有茕茕然的文人孤独却又有市井下里巴人,老少咸宜,诙谐之下却拥有对于生活对于生命深刻的思考。
当问道人的一声应当怎样度过时,可能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背诵起保尔柯察金那一段不因碌碌无为而悔恨。
可蔡澜先生只会对问问题的人竖起中指:屁,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他热爱美食,更是《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的总顾问,很多人恨不得将“食神”这个标签贴到他的脑门上顶礼膜拜,可是对此,他只是淡淡地评价:“我只是全球各地跑得多,吃得各国美食,自然有了审美鉴赏能力。”

告子曾言“食色,性也。”蔡澜先生将这句话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热爱女人,无比炽热。
他曾在《红颜知己》中坦言:小时候读古书,看名画,见诗人携青楼名妓游山玩水,羡慕之极,向上苍许愿,愿在人间一日,能有同样艳遇,死也瞑目。
即便已经结婚,夫妻相敬如宾,蔡澜先生依然抱着火焰般的热情投身到这个荒谬的少年梦中。
2001年他在自传里写自己有47个女友,“如今还在以每年一个的速度增加”。

“世间唯有美食与爱情不可辜负。”他怅然地表示,他做到了前者,但后者还是略有遗憾。许多人批评他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直男癌重度患者,甚至有人嘲笑他:你丁克一辈子就是为了玩女人?
但是啊,蔡澜的丁克,却源于他对这个世界的不信任。
他不信任这个世界会美好,他不愿意将一个孩子丢到一个乱七八糟的世界中。
一个潇洒之人却同时是一位悲观主义者。
真的好笑。
笑完之后才知晓,作为人这个个体,他更愿意将所有的精力付诸到自己这个人本身,哪管清风拂山岗,哪管明月照大江。
活得有趣岂不快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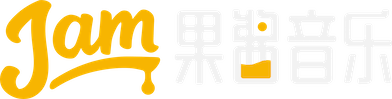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