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摇滚是发源于美国的一个音乐“新发明”,它是个筐子,装什么都可以。每个民族、每个音乐家,都给摇滚赋予了新的意义。
摇滚是发源于美国的一个音乐“新发明”,它是个筐子,装什么都可以。每个民族、每个音乐家,都给摇滚赋予了新的意义。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向往中国。我们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长大的年轻人,向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毛泽东带来的变化让我觉得跟理想很接近。
中国那时候并不开放,我能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信息主要来自《中国画报》《中国建设》等少数几本中国向世界发行的杂志。我现在还记得一个画面:一大群人手捧鲜红的萝卜,这个场景很美。另外,大寨给我的印象也很深。
摇滚是个麻烦
1957年,我在德国小城尼尔廷根出生,并在那里长大。我十五六岁读高中的时候,就经常组织乐队演出。
我最早接触的中国音乐是中国电影里的配乐,那是70年代末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中文的时候。当时,中国电影导演“第五代”已经出道,我常常跟中国驻德国使馆联系,问他们有没有新出的电影可以看。说不定我是德国持续放映最新中国电影的第一人呢,《红高粱》《黄土地》《大阅兵》……这些电影用的音乐都是中国式的,听上去很有力量。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电影将为我搭起走向中国摇滚乐的一座桥梁。
从1984年开始,我几乎每年都有几个月,以研究生的身份,在中国做校际交流,直到1989年彻底搬到中国生活。
有一段时间我在北京电影学院做中国电影研究,跟张元、王小帅这些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特别熟。张元跟崔健也很熟,通过张元,我进入了中国音乐圈。
崔健是很有力量的一个人。那时候他们一般在小地方演,有时候也在大学里演出。我看到他的表演,马上就有鸡皮疙瘩冒出来,我知道这是好东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
那时候的摇滚歌手很爱国,非常关注社会问题。他们创作的歌曲的主题,有些在当时还相当敏感,但他们非常勇敢。很多主题也特别有意思,比如关于光荣,关于责任,这些都是他们通过音乐表达出来的。
当时我觉得中国的音乐很奇怪,跟西方完全不一样,在西方,音乐和观众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在中国,音乐人和观众之间有一道玻璃墙。崔健是第一个打破这道玻璃墙的人。
那时候摇滚是个麻烦,被当成“精神污染”。摇滚乐手也很可怜,没有演出的地方。

“地下活动”
从1989年开始,我在北外教书。我发现,学生们的德语都学得很好,可是他们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跟德国人交流。当时我想,中国的年轻人和德国的年轻人在一块儿,音乐是个不错的话题。我该为他们之间的交流准备点素材了。
当时天坛公园有个地下电影院,我们每个礼拜都在里面做活动。观众里有留学生,也有中国的摇滚乐迷。
崔健在北大就有一个摇滚乐的圈子——他的歌词水平高,好多大学生对他很着迷。
窦唯刚离开“黑豹”的时候,我就跟他认识了。他后来成立的“做梦”乐队在那个年代非常前卫,有实验性。他和崔健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崔健的歌词承载了更多社会意义,而窦唯是在音乐上非常有灵性的一个人。
那时候出现了好多乐队,包括女子乐队“眼镜蛇”和“黑豹”等等……90年代初也开始出版唱片。我还记得“魔岩三杰”中的何勇在《钟鼓楼》里唱道:我的家住在二环路的里边……
那时候我们还不是特别考虑钱,能办就很好。观众需要买票,但票价不贵,主要是给音乐人一个演出机会。场地在北京并不难找,比如跟友谊宾馆说好了,他们常常愿意提供一个地方做活动。但问题是,如果规模稍微大一点,有礼堂和五百个观众的话,就会很麻烦。
1993年1月,我组织了四支摇滚乐队:崔健、眼镜蛇、唐朝以及王勇,以“中国·先锋”项目的名义将他们带到德国柏林。
从政府的角度说,这真是中国的一场非常成功的公关活动。1989年以后,西方媒体普遍觉得中国没有年轻人和年轻人的文化。忽然,一大群摇滚音乐人来了,他们留着长头发。德国的报纸、电视台全都报道了。他们一下子看到了中国的摇滚音乐人:崔健有一点中国特色摇滚的风格,何勇则是用电子音乐加古筝配乐。唯一的问题是歌词需要翻译。不过,上电视节目的时候,歌词被翻译出来打在屏幕下方。地方电视台还请了王勇和唐朝参加一个跟普通观众,包括老太太们讨论音乐的活动,特别好玩。

慢慢长大的爵士节
这次活动完成后,我开始考虑可以在中国国内做些什么。比起摇滚来,爵士乐更容易被接受。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年轻人没有太多机会听到外面的音乐,唯一的渠道就是磁带和CD,对爵士乐更是一点都不了解。中国封闭得太久了,年轻人非常“饿”。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做了8年爵士音乐节的原因。我想把它做成“超市”或是“展会”,让大家各取所需。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文化活动都是政府而非私人能举办的。第一届爵士节规模很小,国外来了四个乐队,加上中国的刘元,演了五场。第一场是1993年10月13号晚举行的。当时没有赞助商,我不过是发挥创意,利用了政府间的文化交流合约——德国歌德学院、法国、瑞士和西班牙的文化单位都与中国政府有演出交流方面的合作。乐队也没有经过我的筛选,而是各个文化单位提供的。所以第一届爵士节,基本上我把能拿到的东西拼在了一起。我们的经济条件特别差,所以不能完全请到想请的乐队来编排一台完备的节目。
当时的音乐和艺术不是被当作一个产业,而是当成政治或者宣传活动。很多公司不敢赞助这个新生事物。我当时去找了拜耳公司,就是推出了阿司匹林新药的那个公司。我对他们说:这个音乐节让很多人头疼,你们要不要赞助一下这个活动?然后他们赞助了一点点。大众汽车是比较早给我们赞助的,在那时候很了不起。因为当时赞助私人的活动基本上是有风险的。而且,能筹到的钱非常少。
我给1994年的爵士音乐节起名叫“等待爵士”。我们一直没拿到批文,直到最后一天。一家有政府背景的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成为爵士节的主办单位。这一届,中国的爵士乐队就多了起来,比如军乐团出身的杜银鲛组建的银鲛乐团。我们给了他们一个比较大的舞台,让还在成长期的他们在知名乐队前面演出。晚上,中外的音乐人们就在一起交流。
那时候的观众很热情,很多人第一次有机会听到在当时看来很奇怪的东西。在民族大学附近的一条街上有好几家烤肉店,好多音乐人常在那里聚会,我总是跟刘元争吵——关于音乐的发展,关于怎么做一个中国特色的摇滚,或怎么把民族音乐包装起来。

摇滚是一段历史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打算在友谊宾馆做一个户外活动,一切都安排好了,演出前两天,我突然接到通知,活动取消了。我们只好打电话通知观众,把所有的票都收回来。还有1999年第一届“喜力节拍”的时候,场地在日坛公园,舞台、布线,全都做好了,乐队也已经请好并签订了合约,却刚好遇到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而日坛公园就在美国使馆旁边。没办法,只能推迟到两个月后。白花了将近两百万。幸运的是,喜力还是付了钱。但想起来真是让人后怕。
不过,我还是蛮喜欢那个年代。那时候有一种保守的制度,你需要去跟保守的制度碰撞出一点空间。那个时代给了我很多压力,有一段时间我几乎要受不了了,可是我又非常满足于当时的生活,非常充实。可以说,那个时候是摇滚(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因为当社会有一种压力和一点矛盾的时候,这种压力和矛盾对艺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源泉。
现在,社会变了,有好有坏。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这些文化活动。比如文化部支持摇滚乐队或是流行乐队去国外演出,学校帮助年轻人安排排练的地方。他们的生活非常优裕,根本想象不出曾经有这样一个时代,要找一个地方“地下演出”。
如今,音乐变得特别“商业”。商业社会的音乐没有那么“危险”,因为“变革”或者“反抗”的概念会被商业消解。不过,我觉得中国人应该和商业保持一点距离,人固然要赚钱,但也需要理想。因为,只能用钱买到的东西,往往会很快贬值。在商业社会,你可以一夜成名,但也可能被迅速遗忘。
现在你要表达观点,不需要一个艺术家替你发声。网络上,你基本可以随便表达自己的看法。而在崔健出道那时候,一些在社会里没有人敢说出的问题都是通过他的歌曲第一次表达出来。
摇滚现在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段历史。理解历史不是一件坏事情。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日益凸显,需要一种年轻的音乐。摇滚和商业肯定是一对矛盾,全世界都如此。音乐不再像以前那么有力量,这是年轻人应该解决的问题。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要创造自己的社会。
30年前,北京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北京很安静,能听得到自行车车铃响,没有现在这种空气微微抖动的感觉。环境变化如此巨大,相应地,音乐家也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今天的音乐。比较前卫的艺术家创作那些很吵闹的音乐,有时候真的不好听。但摇滚是发源于美国的一个音乐“新发明”,它是个筐子,装什么都可以。每个民族、每个音乐家,都给摇滚赋予了新的意义。只有稍微破坏这个“筐子”,才可以创造新的东西。不过,新的是什么样子,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我觉得中国很有意思。可能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上,也很少有这么大、这么快的变化。我在这里,能参与这个过程,参与这段历史,是我的一个机会。我在中国非常幸运的是,跟很多人一起长大了。20多年间结交了好多“战友”,好多事情是跟他们一起做的,好多变化是一起看到的。好多当年跟我一起做摇滚、做音乐的人,都是在社会上还蛮有地位的人,这种感觉非常愉快。能做一些对社会有影响的事情,是最值得我骄傲的。
转自凤凰网
本图文经由摇滚客整理与加工,第三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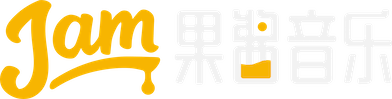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