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最热爱摇滚的人,不是任何一个摇滚乐手,而是每一个被称作骨肉皮的女孩儿。
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骨肉皮,除非丫脑子有病。这是一个带有蔑视意味的叫法儿,没有人会喜欢。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一个别人眼中的骨肉皮,大概是在我刚刚成为一个女人不久。多少有些遗憾,我的第一次不是和我最爱的男孩儿。即使到了现在,我也没有遇到一个最爱的人。
我姑且称自己是一个骨肉皮吧。在这里先普及一下摇滚知识,骨肉皮是Groupie的音译,指专门跟摇滚乐手睡觉的女人,或者学术一些你可以认为她们是“为了钱和出名千方百计主动献身摇滚明星的女歌迷”。北京的圈子里给这样的女孩儿叫“果儿”。“戏果儿”是男的泡女的,“戏孙”是女的搞男的。我不认为我脑子有病,我只是有点儿热爱摇滚乐,只是迷恋那种肉体上的满足。但我不会满世界宣扬“我爱摇滚乐”,那是石家庄那些县城文学青年们爱干的事情,并且把这句口号印刷出来公开发行,唯恐人们不知道。够傻的。
我对摇滚乐没那么了解,我对摇滚乐的全部了解几乎都来自摇滚乐手们的床上。
起床的时候应该已经是中午了,窗帘拉着,我没看表。我看了看睡在我身边的这个男人,睡得很香,他的屁股很好看。我们昨天晚上做了两次,其间我到了三次高潮,我承认他第二次做得比较猛一些。我喜欢看他把头发散开,遮住眼睛,迷乱地,猛烈撞击我的身体。我不在乎发出很大的声音,也不在乎把身体撞得生疼。既然是性交,就得拿出性交的态度来。
我上了个厕所。然后站在镜子前端详自己的裸体。镜子里的我还算年轻,一点都不老,我的皮肤很光滑,肚子上也没有赘肉。乳房也坚挺,虽然不是“非常”大,但也足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了,而且对称,如果我去湖南,应该可以达到应征公务员的标准了。只是我的脸在灯光下显得分外苍白,我摸了摸我自己的脸,脸上毫无表情。也许我有些自恋。我认为我还算好看。
我这么端详了自己一会儿,开始洗脸刷牙,用他的香皂洗过了脸,拿起牙缸里唯一一支牙刷,看了看,挤上牙膏,开始刷牙。刷牙声在这时候显得很空洞。如果配上一段音乐不知道什么效果。吐掉牙膏沫儿,漱口,涮牙刷,把牙刷扔进牙缸,把牙缸放在原来的位置上,并重新摆放好。
我把手提包里的所有东西撒落在桌上,化妆品、香水、两部手机、Mp3随身听、钥匙、钱包、香烟、Zippo打火机、安全套……我穿好衣服之后开始化妆。这动作让我联想到《聊斋》里的《画皮》。
在我眼里,摇滚乐手们有各种风格,但是这种风格和他们在舞台上装扮出来的风格并不一致——甚至有很大的反差。
我曾经沉湎于一个非常棒的吉他手的演奏技巧中,他在舞台上从来都非常稳重,他的吉他比他的为人更加稳重,这是我迷恋他的原因。他们乐队出过两张专辑,反响都很不错,我很欣赏他们乐队的才气,虽然算不上咄咄逼人,至少能让人得到快乐。不要以为我只是一个有着漂亮胸脯的女人,我的审美能力并不低下。顺理成章地,我跟他回了家,他的家布置得井井有条,一如他在乐曲中所铺设的吉他音轨。他热烈地拥抱我,疯狂地吻我,我激情地回应,发出娇弱的喘息。我看到他的吉他放在床边的吉他架上。他拥抱着我摔倒在他淡蓝色的床单上。他的手疯狂地除去了我的衣服。
但是他高超的技巧只存在于舞台之上,在床上,他差得一塌糊涂,每次都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连演奏一首曲子的时间都不到。但是我会安慰他:“没关系,已经很舒服了。”我知道我的笑靥如花,我也知道我的头发有多么凌乱。
镜子里的我真得很苍白,有必要再涂一些眼影,这样会让眼睛显得生动一些。索性再多涂一些,既然生动,干吗不再生动一些?嗯,终于满意了。我把散落在桌上的所有东西塞回到包里边,扫了一眼仍睡在床上的男人,转身出门。门被重重地关上。
2
街上的阳光很明亮,一个女孩儿匆匆地在人群里穿过。
这个女孩儿就是我,如你所知的,你可以称呼我为“骨肉皮”——或者是一个果儿。如果你想客气一些,你可以叫我小麦,这是我的自称,圈子里的人也都这么叫我。到现在为止,你所知道的是:我很年轻;我还算好看;我是一个热衷于和各种摇滚乐手做爱的骨肉皮……其实你对我并不了解。所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跟着我的文字来一点点了解我的故事。
这是北京的初夏时分,街上的风景开始漂亮起来,年轻的情侣们依偎着,穿着好看的衣服。小商贩们努力地吆喝着,但他们也在堤防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城管,那是他们的天敌。出租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过来,经过车站的时候会放慢速度。偶尔会有上下车的乘客。公共汽车一如既往的拥挤,古老国度的人们已经忘记种种礼节与风度,争先恐后地上下车。这一切,在我的眼睛里面并不新鲜,因为我就在这座古老但历史尽失的城市里出生、长大,早已经熟视无睹。
“晚报,北京晚报,晚报,北京晚报……”书报亭的自动小喇叭已经开始广播上了,这才几点,晚报就已经上市了。我没有看报纸的习惯,却听惯了《北京晚报》的吆喝声。这已经成为了北京这个城市的经典环境音。
“要光盘不要?要毛片不要?光盘……”这时几个外地中年妇女的吆喝声,她们吆喝得很努力,但就是太直白了,连点广告语都没有,比如说“欧美最新毛片儿经典”、“日本AV女优的最新姿势”、“如何让口交变得更有味道”。从这一点上来说,新浪的博客频道就做得比较好,没那么回事儿也能把标题变成那么回事儿,怎么惹火怎么来。我从卖毛片的大婶身边经过,没带走一片光盘。
我喜欢北京的夏天,很热,可以穿很暴露的衣服,也可以欣赏别的女孩子们裸露出来的身体,白花花的,像一堆一堆的肉。我喜欢在街道上穿过,也把自己的身体展示给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城市的居民和过客。我只是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一道风景,有时候我在这个城市里沉默,但有的时候,我却必然的,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道风景,我在街上流动,像大多数漂亮的女孩子一样。只是我身边少了一个帅气的男孩子。
我不认为没有男朋友是一个遗憾。虽然我也渴望爱情,但却不希望稳定的恋爱关系成为我的圈套,身陷其中,而失去了自由。我猜想,恋爱往往会让一个人失去自我,你得照顾对方的感受,你还得去关心他,甚至你还得不断地琢磨他的小心思,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啊?他最近没跟别的女人睡觉吧?乱七八糟!女人何苦为难自己?这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我的身体是正常的,我有我的欲望,有那么多男人想跟我睡觉呢,我干吗一定要找一个固定的男人?别替我的生活操心。
我走进西直门地铁站,经过卖艺的盲人的时候,往他的钱盒儿里扔了一张一块钱的钞票。卖艺人的笛音婉转凄凉,经过他的人们都是匆匆而过,没谁被他的音乐所感动。这也是这个城市里熟悉的画面。地铁车厢内很喧闹,很拥挤。年轻的人们兴奋地交流着什么。偶尔会有人接听手机,但是信号并不好,随时会掉线,接听电话的人往往会急匆匆地说:“我在地铁上,一会儿就没信号了……”果然,话没说完,电话已经断掉。因为是周末,没有平时上下班的人群,这已经算是不错的状况。我站在地铁车厢的一个角落,戴着耳机默默听着Mp3播放器里的音乐。周围的人群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摇滚乐或者说摇滚乐手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具体传说中的他们是什么样我已经很难笼统概括,大概不外乎是颓废——愤世嫉俗——不负责任——我从没有想要任何一个人对我负任何责任。你不觉得“负责”是一个很好笑的词吗?它是动词?还是名词?要是谁大发善心要对我负责任,我只能落荒而逃。
车内广播响起, “……各位乘客,欢迎您乘坐北京市地铁列车。复兴门是换乘车站,请您在站台中部下台阶,换乘一线地铁……”提醒我该要下车了。
3
这是那种北京最普通的公用电话亭,橘黄色,有些旧,在半圆形的内侧里面贴满和写满了各种小广告,办假证件的、招工的、同性恋交友的,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报纸上不都喜欢这么形容么。
我在等一个电话,这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习惯。我几乎已经忘记了是怎么接到的他的第一个电话,是一个下雨天吧,我躲到这个电话亭避雨,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这年头儿,谁还会打传呼呢?或者是谁用这个电话拨过对方的手机吧?电话铃是在响得刺耳,索性把它接起来。
“喂?”我说。
“我只是想跟人聊聊天儿。”电话那头是个说话声音很好听的男声。
我们就这么聊了起来。那天聊得很好,于是他偶尔就会打这个电话,如果我恰好经过这里,我会跟他聊起来,像一对老朋友那样。逐渐地,也就形成了默契。这个回忆很美好,我几乎都不愿意去回忆,我不知道回忆多了,会不会让回忆变淡。电话铃打断了我的回忆,我知道这电话是找我的。
“你是不是好几天没打过这个电话了?”我接起了电话。
“也不是。”他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好听。
“有什么特别想说的话吗?”我点上一支烟,望着周围的霓虹灯和来往的车辆。
“没有吧。我打这个电话只是为了跟你聊聊天,并不一定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听你说点儿什么也好。”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生活很无聊,每天给自己找乐子,稍微琢磨点儿理想什么的我都替自己觉得害臊。”
“北京太大了。这么大的城市,能有一点儿理想也是件很难得的事情。”
“是啊。”我抽了一口烟。
“你在抽烟?”
“是的。”
“等我也点一根。”他在那边点烟,“你看过《海上钢琴师》吗?”
“《1900》?”
“对。他说:陆地对我来说是一艘太大的船,太漂亮的女人,太长的旅程,太浓烈的香水,无从着手的音乐。我永远无法走下这艘船,这样的话,我宁可舍弃我的生命。”
“所有那些城市,你就是无法看见尽头。在那个无限蔓延的城市里,什么东西都有,可惟独没有尽头。拿一部钢琴来说,从琴键开始,又结束。你知道钢琴只有88个键,错不了。你把我推到舷梯上然后扔给我一架有百万琴键的钢琴,百万千万的没有尽头的琴键,它们没有尽头。那键盘是无限延伸的。然而如果琴键是无限的,那么在那架琴上就没有你能弹奏的音乐,你坐错了地方,那是上帝的钢琴。”我接着他的话题,背诵着《海上钢琴师》的台词。只是我不确定顺序对不对。
“你居然能够背诵下来。”他显然有些吃惊。
“因为我也活在一艘巨大的船上,我找不到走下去的路,也没有走下去的勇气。”我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把它踩灭。
“我却是上了这艘船——1900可以坐在他的钢琴前面,但我不知道我坐哪儿。”
电话那头的声音永远不温不火,应该讲对我很有吸引力。在这时候的我,仿佛是个淑女一般,毫无狂妄、放纵、肆无忌惮的影子。我知道,我说话的声音也很好听。我不得不承认,聊天是需要对手的,需要有同样的心智,也需要有同样的话题。我喜欢在电话里跟他聊天,但是我不知道他下一个电话会在什么时候打来,当然,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找到我。
这是一个游戏。

4
我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去新豪运酒吧,就在女人街那边。原先的时候,大伙儿都去太阳宫那边的豪运酒吧,北京政府进行市政规划,把老豪运酒吧给规划掉,在女人街那边规划出一条酒吧街,取名叫星吧路。于是原来豪运酒吧的老板就在星吧路又开了一家新豪运,结果大伙儿就都来这边儿玩儿了。老豪运的时候我曾经去过几次,但那个环境太逗了,大厅是摇滚演出的地儿,来的都是摇滚乐队和热衷摇滚的铁托儿,而包间,则有专门的陪酒小姐,穿着暴露,来的客人也跟摇滚乐没有任何关系。你要愿意出钱完全可以把她们带走做你爱做的事情,但是猫王说过:从隔壁的奶牛身上就能挤到牛奶,我他妈养牛干嘛?那地儿太奇怪了。
其实关于北京的摇滚演出场所,就能写出一大篇儿文章,不少爱看演出的人都曾经写过。其实北京就那么几个演出场所,比较早的忙蜂、CD咖啡、莱茵河声场、老豪运、嚎叫俱乐部、开心乐园、芥末坊、17,后来的新豪运、有戏、河、仁CLUB、无名高地。基本上这些地儿我都去过。虽然风格各异,但大抵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不外乎是舞台上摇滚乐队演出,台下的歌迷们尽情发泄,怀揣小想法儿的男男女女各自得到想要的东西,带着满足回家,然后达到更大的满足。
星吧路酒吧街一片繁荣景象,种种装扮的人群,没有任何一个人显得突兀。漂亮的女孩子三五成群,纹身、长发、叼着烟卷盘道的摇滚乐手们纷纷酷到一定高度。有人开始跟姑娘搭讪,有人保持冷漠。从新豪运酒吧里传出的背景音乐节奏清晰,主唱的声音仿佛能穿透人的心脏;各家酒吧的不同风格的音乐掺杂在一起,很有夜晚的繁荣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任何人都没有缺少活力的道理。郑钧开的LOGOS就在新豪运对面,可惜我没进去过,也没在这里见过郑钧。郑钧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别误会,我没跟他睡过,而且据说他是一个特好的男人,对老婆很专一,估计就算是我主动跟他睡他也会拒绝我。就不丢这个人了。
有时候我会想,要是写一本关于摇滚乐的书,说不定会畅销,毕竟这是一个游离于普通人视线之外的特殊的人群,毕竟我知道那么多摇滚乐手的私密。但是摇滚乐在媒体和唱片公司的双重蹂躏(镇压)之下,已经越来越成为一个不靠谱儿的概念。我曾经问过不同的摇滚乐手——“在你的心目中,摇滚到底是什么?”
在床上,蓄了一头长发重金属乐手A搂着我,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摇滚实际上是一句黑人的俚语,代表的是人们做爱的动作。摇滚代表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了我自由的生活。”
在酒吧,剃了一个鸡冠头的朋克乐手B坐在我对面,心不在焉地告诉我说:“摇滚是打破一切制度,摇滚是和平与爱,摇滚是暴力与反抗,摇滚是墙上的一块砖,摇滚是中央公园的一片草莓地……”
在出租车上,英式摇滚乐手C把我的手攥在他的手里,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说:“对我来说,摇滚首先是一种精神状态,其次才是音乐。至于你的技术、你所要阐述的所有理念,都是为你的精神状态所服务的。”
我所乘坐的出租车缓缓停在新豪运酒吧门口。付钱,下车。如果当时你也在,你会看见车门打开之后,浓妆艳抹的我从出租车上下来。然后你会看见我点了一只烟,扫了一眼酒吧门前的人们,当然,你也在其中。然后我从手提包中取出一部手机,关机;再取出另一部手机,打开。然后,我把才抽了几口的香烟扔在地上,踩灭。最后,你会看见我款款走进酒吧,留给你一个美丽而空虚的背影。
5
舞台上,声音碎片乐队正在演出。说实话,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支乐队,非常有才气,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乐手演奏水平也不俗气。尤其是他们的主唱马玉龙,嗓音太好听了,歌词写得完美无缺,如果不是因为他不太帅,我一定收了他。
我站在舞台下看了一会儿,吉他手李韦把头发剃成一个特傻的平头,但他的演奏依然那么有味道。新加入的键盘手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显然他已经融入了这支乐队。最吸引我的还是主唱马玉龙,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这首歌曲叫《优美的低于生活》,只风琴的前奏一起,就足以让现场气氛热烈起来了。
把歌声还给夜晚/把道路还给尽头/把果实还给种子/把飞翔还给天空
剩下的,让它们美好/从容的埋藏得更深
最后让这纷乱的一切都单纯的低于生活
nayeah!只有内心远过空旷/ nayeah!梦到了丰饶的草原
相爱吧,终有一散的人们/你失去的不过是童贞
等时光用尽了青春 /你早已优美的在大街上溶化
我的帅哥很关心地问我:“你喝点儿什么?”
我没客气:“就喝你们的青岛吧。”于是他递给了我一瓶青岛啤酒,跟我碰了一下。
我说:“你好像是一个吉他手,我应该看过你的演出。”我没再理会坐在一旁的另外两个人,此刻,在我的眼睛里,只有我的这个帅哥。
他说:“我们乐队演出不算多。”
“果味木马乐队?”其实我从刚才就看他有点眼熟,印象中是看过他的演出,但又不太确定,听他这么说,我才突然意识到,他一定是果味木马乐队的吉他手,只是我忘记了他的名字。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还真知道。”
这就对了。于是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帅哥自我介绍说:“刘钊。文刀刘,李大钊的钊。”对!就是这个名字。这么好听的名字我怎么就给忘了呢?
我也顺便抛出了我的名字:“我叫小麦,大小的小,麦子的麦。来,为咱们认识干一杯。”刘钊和我又彼此碰了一下手中的啤酒。
其中一个帅哥不满意了:“噢,你们俩聊这么热乎,就不管我们啦?跟我们也介绍介绍。”另外一个也附和着说:“谁说不是?”他们两个也分别说了他们的名字,但是我没事儿去记他们俩的名字干嘛?
“认识你们很高兴。”于是我举起酒瓶,分别跟他们两个干杯,我笑得很开心,风情万种。
6
在北京的摇滚Party上遇到像刘钊这种没出名的小乐队的吉他手根本就是件稀松平常的事,一点都不稀奇。在Party上往往能遇到各种摇滚名人,但是我很少见到有人拿着个小本本请他们签名,大家都是来当观众的。顶多会有人跟朋友嘀咕一句:“瞧,那谁来了。”“那谁”之所以出现在这样的场合,是因为这里好玩儿,或者是来看看别的乐队玩儿成什么样子了
崔健经常会出现,一点儿也不神秘,从来不会像那些三四流的电视小明星们一样有事没事带个大墨镜,但是却没有一次不戴他那顶标志性的白帽子。如果恰好有记者在场,问他一些什么问题,他也会压低声音做出回答,但这种情况很少,崔健就是来做观众的。看得出来,老崔对摇滚圈还是很关注的。虽然江山代有才人出,但也只有崔健能够独领风骚二十年。别看现在的年轻一辈摇滚青年个顶个儿的玩儿风格,其实老崔比他们都有风格,老崔才是一直走在摇滚前列的领路人。
窦唯不太爱说话,但我跟他说过话,他语速不快,稍微有一点点结巴,如果我着急的话也会有一点结巴。在我眼里,窦唯是个好男人。他不是一个侃侃而谈的人,不像其他这个圈子里的人,他会像一个老朋友一样跟你说些近况,比如正在和什么人合作什么样的音乐,比如他希望他的音乐不要被误读。我相信人都是需要互相尊重的,像窦唯这样不善表达的人,抱着八卦态度的娱乐记者绝对是讨厌的人,所以当他被逼急了的时候才会泼他们一脸可乐,或者追到报社去讨要一个说法。他曾经给我留过一个电话号码,但我从来没有拨打过。
朴树其实最早也可以算是个玩儿摇滚的,只不过他成功的成为了一名深受大众喜爱的流行歌手,其实他的音乐做得非常不错,把他放在流行歌手堆儿里实在对他是种贬低。朴树是个非常喜欢混par的人,经常能在各种摇滚场合见到他,包括这种普通的周末摇滚party。朴树很注意自己的仪表,就算是大夏天也会穿一件厚厚的牛仔外套——如果他认为那样好看的话。他经常是一个人来,然后坐在吧台一边看演出一边喝啤酒。他其实就是来当观众的,如果有女歌迷找他签名或者合影的话他也不会拒绝。
清醒乐队的沈黎晖除了是一个乐队主唱之外,另外一个身份是摩登天空唱片公司的老板,如果是他们公司的乐队演出,他基本上都会出现。他不抽烟,基本上都是拎着一瓶啤酒站在那儿看,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跟公司的同事一起来,有时候他身边站的是某个乐队的乐手。一些没名气的小乐队很是希望这位摇滚圈儿的老板级人物能相中他们,能跟摩登天空签约是不少地下乐队的理想。我对沈黎晖这个人印象不坏。
刘以达我也见过,就是香港“达明一派”的吉他手,如果你熟悉香港流行音乐的话你会知道这个人。如果你不太了解香港音乐,没听说过“达明一派”,对香港电影比较了解的话你也可能知道这个人,在周星驰主演的《食神》中,刘以达同学扮演了著名的“梦遗大师”,就是那个会横着跑的、神出鬼没的“梦遗大师”。在《大内密探零零发》中经常找零零发看病的人妖也是他演的。很没架子的一个人,像普通老百姓一样站在人群里看演出,连根烟都没抽。那次大概是在国内拍什么片儿,趁周末过来感受一下北京摇滚乐的氛围。就见过那一次。
像高旗、李延亮、骅梓、陈底里、张浅潜、姜昕什么的在party上也都见过,我还见过一次作家棉棉,是跟姜昕一起来的。我曾经挺喜欢棉棉写的小说的,把青春记录得鲜血淋淋,痛快不已。据说棉棉曾经也做过骨肉皮,她还曾经有过一个搞摇滚的男朋友,据说就是“在地安门”的左小祖咒。
7
既然说到了姜昕,我在这里索性八卦一下。姜昕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从最早的《花开不败》,到这两年的《纯粹》,都是不错的专辑。这里我不想谈她的音乐,就谈她的八卦。其实也不算很八卦啦,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
姜昕最早出现在摇滚圈是作为当时黑豹乐队主唱窦唯的女朋友,那时候她从大学退学,一门心思爱着窦唯,据说窦唯也很宝贝这个女孩儿。感觉姜昕是那种特没城府的女孩子,很单纯,成天儿就是跟这些摇滚乐手们混在一起,几乎那就是她的全部生活。当时的摇滚圈子并不大,不外乎就是黑豹唐朝那几支乐队。后来姜昕和窦唯的感情除了问题,是因为出现了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不是别人,就是当时正在香港发展的北京女歌手王菲——当时她的艺名还叫王靖雯。我不太了解其中的具体情况,反正后来王菲怀了孕,结了婚,为窦唯生下了一个女儿。关于这段三角恋是在错综复杂,据说里面还有当时黑豹键盘手栾树的一些事情,这里就不谈了。
跟窦唯分手之后的姜昕也成为了一个歌手,并签约了天蝎唱片公司,那家唱片公司的老板叫郭大炜,据说也曾经是位摇滚歌手,具体就不去考证了。可以肯定的是姜昕成了郭大炜的女朋友。也是在那时候,姜昕推出了她的第一张专辑《花开不败》,其实这张唱片做得非常棒,可惜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所以知道姜昕的人也就不是很多。
后来天蝎唱片关了门,她和郭大炜也分了手,成了唐朝乐队吉他手郭怡广(Kaiser)的女朋友。关于这段恋情我不是很了解,但我知道他们一起住在太阳宫附近的芍药居小区,一起住的还有唐朝主唱丁武,以及当时嚎叫俱乐部老板、后来的嚎叫唱片负责人吕玻。
再后来,姜昕和摩登天空签了约,推出了第三张专辑《纯粹》,而这时候,陪在姜昕身边的人已经换成了著名鼓手、有“中国鼓王”之称的鼓三儿张永光。张永光最早是崔健的鼓手,《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张专辑里的鼓就是他打的。而且,张永光和姜昕已经是好多年的朋友,从她最早一张专辑开始两个人就有过合作。这时候姜昕和张永光已经结婚了,感情很好,我曾亲眼见到姜昕小鸟依人地依偎在她爱人的怀里,幸福得像只小鸟。
你能说姜昕是个骨肉皮吗?我曾经和一个姜昕圈子里的朋友——当然也是一位摇滚乐手聊到过关于姜昕的这几段恋情。那个朋友说:其实姜昕算很幸运了,能有几次这样刻骨铭心的恋爱,而且这几次都非常用心。我想也是,一个女孩子能死心塌地地爱,而且被爱,这已经足够幸福了。如果有人能这么爱我,而我也同样如此爱的话,那我也就足够幸福了。从这点上来说,我很羡慕姜昕。
8
这天晚上我并没有跟任何人回家,刘钊有女朋友,而且住在一起,就算他有想带我回家的心估计也没这胆量,况且他有没有这个意思我还真不太清楚。
我突然很想接到我那个陌生朋友的电话。我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一个人散步到公用电话亭,在电话亭前徘徊。
抽烟。用我的Zippo打火机点烟。发出清脆的响声。
看过往车辆。形形色色的车从我面前开过。
霓虹灯闪烁的街道上,偶尔有摩托车驶过,那是不肯循规蹈矩的年轻人的嗜好。
骑自行车经过的人朝我观望。我想是因为我的衣着过于暴露的原因。也许他们把我当成了性工作者,说不定很想停下来跟我搭讪,只是缺少一点点勇气。
我所期待的电话铃声一直没有响。
我蹲在地上抽烟。捡一枚小石头,在地上画来画去,我自己都不知道画出来的是什么图案。把烟头架在中指和拇指中间,用力弹出去,掉到马路中间,渐渐的灭掉了。
我在公用电话亭前的徘徊,慢慢幻化成了一支孤独的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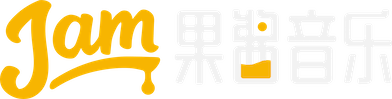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