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夏结束,从线下到线上的演唱会狂欢也已经落幕。
可是在这场从盛夏到深秋的相聚里,我依旧充满了遗憾。
这些遗憾与节目无关,只是我对一些乐队的期盼不止如此,比如有一种期待叫做我想听布衣唱一首《三峰》。
西北的风沙会在他们的音乐里化作恋人的缱绻低语,漫长的前奏会自动筛选没有耐性的听众。
1995 成立于宁夏的布衣,有一种西北大汉独有的质朴洒脱,这种来自秦腔的气质浸润在旋律和嗓音中。
在乐夏的舞台上,来自西北的汉子们唱出最真诚的歌,用他们音乐里的生命力打动我们,然后像个深藏功与名的大侠,潇洒地转身离开。
同样来自西北的野孩子,第二季因为音乐理念不同直接中途退赛,他们的音乐里也有种远离城市喧嚣繁华的自然宁静。
黄河流域、黄土高原,在这片以黄色为基调的土地上,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名字和声音。
不同于温柔婉约的南方,西北的风沙粗粝磨人、黄河流水奔腾席卷着整个黄土高原,在这种环境下催生出来的西本音乐,自带一种苍茫雄浑。
西北人好像天生就会唱歌,吼出来的那种,不刮风的日子里天空透蓝,风沙弥漫的时候尽情喊上几嗓子黄土高坡也被喊得透亮。
苏阳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歌声里有着对土地和生命的记录,他的声音自由而高亢,让来自自然的声音成为音乐的一部分,也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我始终热爱《贤良》里他纵情地呼喊,天然又纯粹。
生长于黄土高原的苏阳早年间或许也曾被西方重型摇滚乐所诱惑,但在辗转之后他还是没能忘掉自己的根在哪。
那是骨子里抑制不住的关于黄土地关于黄河水关于沙漠关于绿洲关于绝望关于希望关于想有个婆娘的呐喊。
那是融入血液的放荡不羁走马关西,那是呼吸里的猎猎风尘。
它代表着黄土高原乃至整个西北的一种精神:热情、勤劳、坚忍、顽强、朴素、固执。
苏阳突破了摇滚乐和民族音乐的界限,歌唱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鲜花、劳动与爱情。
他表达着无数黄土地和蓝天之中挣扎的升斗小民们最基本最真实的想法:活下去,像拉拉缨一样强韧的活下去。
俗世的“贤良”让他刺痛又不屑。
另一个扎根于民间的西北音乐标志人物,是自称有些歌唱的很骚气的张尕怂。
每次,他有些歌确实很骚气,和二手梁龙的骚还不一样,里面有一种粗野的真实。
让人一听就是屌丝的生活写照,一边是乐呵呵的自嘲,另一边是赤裸裸的无奈。
在这样的屌丝消解里,他的很多歌都带着一股子难登大雅之堂的“粗俗”,但是粗俗得可爱。
从张尕怂的音乐里,我们能感受到那是一个个真实的生命,他们是生长在黄土高坡上也被困在其中的真实的人,有欲望、有过往。
在唱歌的同时,他也在向我们讲述一些接地气,却又很真实很柔软的东西。
在用生活写出来的音乐里,有他对生命的敬意。
谈论西北的民谣,离不开张玮玮和野孩子。
前段时间,张玮玮的新专《沙木黎》发布,新的尝试带来了新的感觉,但我还是对当初那张《白银饭店》念念不忘。
《白银饭店》是一张要从第一首一口气听到最后一首的专辑,娓娓道来里,是白银这个小城市的故事,也是张玮玮的故事。
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座空空的米店,唱歌的人走心,听歌的人也走心,歌的背后,是生活。
有人说“西北是中国民谣的根,兰州是西北民谣的魂。”
《兰州兰州》这首依托在兰州基底上而唱的歌,不只是一首歌,它还代表着一段有关于西北的记忆和那些过往遇见的人。
低苦艾的歌里有旷野风沙的气息、粗粝的底色搭配生动的旋律,将兰州这座城市唱得灰暗而美丽,指引所有人大漠的方向和回家的路途。
西站西站,上车就走,有座位。
白马浪,到了。
苏阳、张尕怂在人间来去、大俗大雅,张玮玮的幽怨之情娓娓道来,低苦艾顶天立地,布衣往事无牵挂,野孩子黄河之水永远奔流。
还有已经提累了的崔健、西安三杰、赵牧阳和黑撒、郭龙、马飞、吴吞、马条、张浅潜……
西北的样子,西北人的性情,在他们的歌里就能听到。
西北的风沙里种不出玫瑰,但能催生出中国摇滚的萌芽。
当丰富的民俗音乐融合了摇滚乐、西式的民谣表现手法,就形成了风格鲜明的中国民谣摇滚或者说是民宿摇滚的一个重要部分。
1988年,中国唱片集团发行了《西北风》唱片集,崔健的《一无所有》被收录其中,中国摇滚从粗犷豪迈的西北风格出发。
敞亮的旋律、歌词搭配上民族乐器,西北的豪爽之气裹挟着风沙席卷而过,人们的生活被具象化,也被真实地记录。
2019年,苏阳拍了一部纪录片《大河唱》,记录黄河流域传唱千年如今却已经日渐式微的三种民间音乐形式 :三弦、皮影和秦腔。
当时的排片少得可怜,后来剪辑后上线B站,播放量至今也不到19万,但只要是看过这部片子的人,都一定忘不了其中那些鲜活的生命。
在影片里,只有忠实的记录和好听的歌曲、配乐,没有旁白的解读,也没有对日渐式微的传统民间艺术的俯视或怜悯。
他们只是记录,在演员一边唱歌一边说出来自哪的时候,镜头正好切换到他的家乡,家乡贫瘠的土壤和旁边树立的风力发电机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这些普通艺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都在这片土地上。
镜头下是灰色的世界,天色苍茫,忧虑的梯田层层叠叠,遥远的天边春雷滚滚。
“这最开始就十二个人。我六个太爷,带着媳妇,住在这了。”这句话,让我想起马尔克斯笔下那个隽永的故事。
他们是演员,也是庄稼汉,拿起乐器、装扮上台之后,他们代表艺术,唱念做打样样俱全。
可是下台的那一刻,他们就回到了人间,把三弦换成锄头,用庄稼人的朴实支撑起一个古老农耕文明的延续。
当苏阳的音乐与戏台上的民歌闪回拉扯,当舞台下听歌摇旗的年轻人和戏台下寥寥无几的老年人重合,你就会意识到,音乐将一切传承了下来。
当城市与农村、现代与传统、工业与农耕重合。
当王洛宾老先生唱起那首《永隔一江水》,当无数精彩却没落的民间艺术在这个时代找到了传承,我们的摇滚也就有了雏形。
西北音乐人的身上有股江湖气,也有一种独特的诗意,是当年的大漠孤烟直,也是如今的西北偏北。
漫长的西北风作用下沙尘年复一年地堆积,风沙孕育出了黄土高原,也孕育了接地气的西北音乐。
风声呼啸间,是一代又一代民间艺人的传承和无数普通人鲜活的一生,他们生活在黄河边,听着说书,唱着花儿……
民间传统艺术或许逐渐衰败,甚至有一天无人知晓,但是传承不绝。
或许有一天,已经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后,有人会在黄河岸边捧起一抔沙,种下一棵树,轻声哼唱:“你是世上的奇女子呀,我就是那地上的拉拉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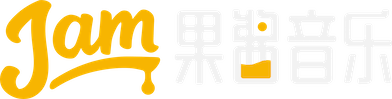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