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摇滚巨星们纷纷陨落时,我才反应过来自己正在告别摇滚乐最光芒万丈的时代。
3月,才宣布重组的传奇摇滚乐队pulp乐队发出讣告,贝斯手史蒂夫·麦基离世,享年56岁。
7月,光头女王爱尔兰女歌手Sinéad O’Connor去世,享年56岁。
8月10日,5天前,摇滚巨星小糖人Rodriguez遗憾离世,享年81岁。
小糖人去了天堂。
私以为,没有一位Rock star的故事比他的更魔幻现实主义:
在美国底特律,他是一名底层工人。
干着最脏最累的活,住着最老最破的房。
没人在乎他的音乐,没人在乎他的生活。
但在南非,他是一位举国闻名的摇滚巨星。
人们将他的影响力比作猫王,将他的创作才华和鲍勃·迪伦相提并论。
更进一步,当时深处革命烈途的南非人民群众还将他视作精神领袖,领导他们迈入新天地。
小糖人的伟大之处,当然在于他创造的音乐;
但更在于,作为一个人,他上得了天堂,下得了地狱,且能在两种人生之间自然切换,处之泰然。
或许,天使游荡人间,便是这般模样。
小糖人西斯托·罗德里格兹出生于1942年,父亲是墨西哥人,母亲是美国人。
至于为什么名字里会有Six,是因为他在家中排行老六。
家乡底特律,美国的汽车之城,犯罪之城。
在暴力与毒品丛生的街头,小糖人抱起了一把吉他,少年时代就早早成为一位歌手,在夜幕下的各种酒吧卖唱。
1969年,他终于签入唱片公司Sussex。这家唱片公司的老板克拉伦斯在业界非常的有名,江湖人称音乐“黑人教父”。
然而,高手也有失手的时候。
次年,首张专辑《冷事实》发行,专业制作团队给出的评价是:
“在这个年代,唯一能和他媲美的唱作人,或许只有鲍勃·迪伦了。”
结果,专辑卖了35张。
唱片公司不甘心。
1971年,再次花下血本打造小糖人第二张专辑《从现实中来》。
结果卖了6张。
顺理成章地,小糖人丢掉了“音乐”这碗饭,回到底特律,回到街头,回到底层。
在圣诞节的前两周,唱片公司将他解雇。
就像他的歌词写得那样“ 因为我在圣诞节前两个星期丢了工作 ”。
他在建筑工地卖起苦力,每天或者木屑和灰土回家,勉强靠此为生。
音乐,成了天方夜谭,被狗日子束之高阁。
觉得恨,但是离不开。大概,命定如此。
这个故事讲到这儿其实平淡无奇。
毕竟怀才不遇,泯然众人的故事才是真实剧本。
然而,蝴蝶效应真的存在。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一位美国女大学生假期前去南非,看望她的男友。
她随时携带的行李中,恰好就有那张压根无人问津的专辑《冷事实》。
七十年代的南非几乎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
人们没有电视,消息闭塞;
任何文艺作品都必须接受疯狂的审查,动不动就是封杀。
此时,无意中漂洋过海的小糖人罗德里格兹的歌声突然出现了。
一首《Sugar Man》就像一颗原子弹一般,引爆了南非社会。
歌中对性的直言不讳,对自由浪漫的追逐,对政治制度的质疑,是南非人民闻所未闻的。
可统计范围内,《冷事实》狂卖了50万张,而彼时,整个南非也只有4000万人。
对于七十年代的南非当局来说,小糖人的歌显然是无法容忍的。
当时,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尚未废除,社会情绪像一根快崩断了的弦。
人们需要一首歌,需要一个人来为他们指引方向,引渡他们到达自由的彼岸。
当局者当然不答应,下达销毁小糖人所有作品的禁令。
然而,这封禁令最终却成为了小糖人被举国传唱的助推剂。
因为人们已经纷纷揭竿而起,成为了可以迅速彼此连接的火苗。
在70年代的南非,小糖人的歌是圣歌,也是禁歌。
然而,对于改变了国家命运的民族偶像,整个南非却没有人知道小糖人的来历,人们只能抱着专辑上的照片作无用功的揣度。
他实在太神秘了。
后来,流言四起:
有说他饮弹自尽;
有说他嗑药而亡;
还有说他在舞台自焚。
认为他尚在人世的南非人少之又少。
多年以后情况依旧如此。
人们想不通,若不是已经告别人世,20年之后的南非已经回归到国际大家庭,顺利进入民主社会,这位“功勋卓著”的超级明星怎会不露面?
终于,1997年8月,一位有志之士联系到了《冷事实》的制作人。
制作人说,小糖人还活着。
听到这个爆炸性消息后,他立马在南非的报纸上刊登出文章《寻找耶稣》。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建立互联网论坛,寻找小糖人。
巧的是,小糖人的大女儿伊娃无意间发现了这个论坛,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就这样,1998年3月6日,成为了南非载入史册的一天。
小糖人西斯托·罗德里格兹,南非人民心中的歌神,在歌曲流传在南非28年之后,第一次踏上了南非的舞台。
这是一场跨越了28年时光,跨越了自由、民主、革命血肉之旅的会面。
演出的前十分钟,全场起立,没有音乐,只有掌声,欢迎着自己的信仰。
小糖人开场的第一句话是:
谢谢你们让我活着。
雷鸣般的掌声仿佛无声回应着:
谢谢你让我们活着。
演出连办了六场,座无虚席。
他把南非巡演的大部分收入都给了家人和朋友。
然后,自己像没事人一样回到了美国底特律居住了40年的房子里,继续自己打着零工的退休生活。
在女儿的口中,他是一位比其他大多数父亲更勤劳的父亲,仅此而已。
有人问他:你喜欢现在在美国的工作吗,它可完全与音乐完全无关。
他的回答是:
喜欢,因为可以循环血液,保持健康。
时间来到2006年。
一位名叫马利克的瑞典人在南非旅游时偶然听说了小糖人故事,发誓必须将它拍成纪录片。
六年之后,影片拍摄完成,最后得到了31个大奖,包括2013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
拍纪录片时,马利克等人叩门拜访,劝说数次,才说动;
2013年,奥斯卡颁奖时,他拒绝了邀请,把功劳全部归于剧组人员。
墨镜下的深邃眼神,平静一如往常。
这是他的选择。
选择保留一个游吟诗人最后的纯粹。
再十年之后,2023年时听说他的消息,已是离世讣告。
传奇落幕,没有如潮式的缅怀,甚至在网易云音乐上还没打出他的全名。
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我心目中的伟大地位。
走上巅峰已经是常人所不能及;
而能从巅峰上顺利走下来,更是难上加难;
他却能在两种人生之间走得如此从容,如此自在。
一个国家里苟且谋生的修理工,却是另一个国家火了二十多年的摇滚巨星。
只有绝对忠于自我的一个人,才能在两种人生之间平静踱步,在平行时空中自由切换。
他双手干着最脏、最累的活,歌喉却唱着灵魂中最美、最动听的歌。
纪录片中有很多幕,小糖人正缓步走在雪地里。
他低着头,手插进口袋,走得很慢,很认真。
或许,生活就是风雪天中的一场旅程,你我都是雪地里的行人。
我会记住,这位雪地里埋头赶路的人,陪我走过漫长一程。
天堂多幸运啊,多了一首《小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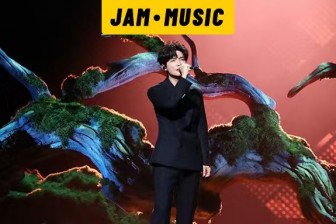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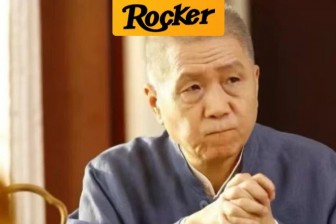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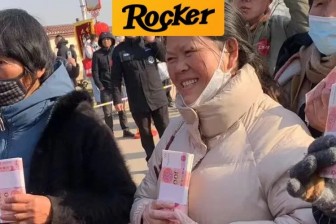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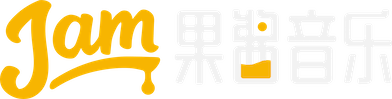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