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马拉松。
百八里秦川上,有一位“宁可痛苦,不要麻木”的农民刘小样。
今天的主人公也是一位农民,耕耘在山东淄博,名为叫杜深忠。
他应该是一位小说家、一位诗人、一位音乐家,但他偏偏就是一个农民。
作为农民,杜深忠并不称职,因为他每天都在不务正业。
不务正业到什么地步?
买不起宣纸,就一首握毛笔,一首拿着水盆,毛笔蘸水,蹲在地上练书法。
投进门来的光,在水泥板上铺成天然的宣纸,任由他驰骋疆场,免费。
按他的意思,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没什么值得歌颂。
每一寸都是血地。
他的故事被记入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即使影片豆瓣评分9.3,拿了龙标,上了院线,获了23个大奖;即使他曾受邀去鲁迅文学院进修4年,但这些光环都没有改善杜深忠的生活。
他还是那个皱纹比山壑更深的农民,种着连年无人问津的苹果。
杜深忠与《乡村里的中国》导演焦波第一次碰面是在自家门口,那天他正蹲在地上拿着毛笔沾着水在地上写书法。
他对焦波说:
“老师,这个透进门框的光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纸。”
见到摄影组,杜深忠并不畏惧镜头,也并不羞涩,文化人的到来反而激发了他的表达欲,他接着补充道:
“我在上面尽情地挥毫泼墨的时候,什么困难、什么挫折、什么无奈,包括我老婆无尽的唠叨,全都荡然无存,我完全沉浸在这个光影的享受当中。”
这么浪漫的一句话竟然从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农民嘴里说出,焦波恍惚了。
这哪是农民,这简直是艺术家!
事实上,杜深忠已经搞艺术搞了大半辈子,学生时代就一头扎进了文学里。
摘抄诗、写日记,对于书籍狂热的爱让他每周末可以翻阅两个山头去新华书店借书。
那时他也成日写小说,写这片养育他的土地,写吃人的封建村落,并且给大大小小的编辑部寄去。
结局是都被打了回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莫言、成余华。
35岁那年,高龄未婚一心寄情于文学的杜深忠迫于压力成亲了。
不过人生也给他开了个玩笑,当他认为这辈子就被这座山村圈住时,鲁迅文学院向他抛出橄榄枝。
在和张兆珍结婚第二天,杜深忠拎上背包,手里攥着借来的200元钱,背上自己的文学梦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
看似杜深忠离自己的理想进了一步,实则又是另一个深渊,系在脖子上的绳索还被牢牢地拴在那片土地上。
在北京的生活除了忍受贫穷,还有心灵上的煎熬和自我怀疑。
北京太大,文学世界太浩瀚,有才的人太多,杜深忠顿感自己的渺小,他说:
“天下的好故事都被写尽了。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有只言片语塞进书里吗?”
一天天干瘪的钱包,永远石沉大海的稿件,杜深忠失望了,退缩了…….
他想,或许自己这辈子只能做个农民。
逃不出时代的五指山,也没有天赐才华的饭碗。
他又回到山东,回到杓裕村,带着自己的自卑和懦弱,躲了起来。
书籍让杜深忠看见了沂蒙山区以外的世界,成为这个农民灰暗生活里的一束曙光,也成为他跌入痛苦深渊的一道闪电。
杜深忠生活的杓裕村是怎样的?
是百年老树被挖走时,农民脱口而出的移情愿望:
给这棵树办了农转非(农村户口转非农村户口)。
是杜深忠回忆起曾经因外出打工而落下的13颗牙齿。
他说,那是拿人肉换猪肉吃。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而外出务工对于他,对于杓裕村的农民来说,没有精彩,只有无奈。
或许你认为这是危言耸听的故事。
在村里蹲守一年的摄制组记录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邻居张自军在贵州打工,从八米高的架子上掉下来,摔死了。
杜深忠听着,忘了抽烟。
按照村里的规矩,死在外面的人,灵棚不能进家门,只能摆在村头。
亲友们从家里往灵棚走,哭丧着:
“我的兄弟,我的亲兄弟。”
下葬时,张自军的儿子站在棺材旁发问:
“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
身旁的老人愣着,回答道,不小,不小。
最终建筑公司赔款55万,一大家子人迅速因为这笔赔款吵得四分五裂。
孩子当然不懂。
不懂爸爸去了哪里,不懂亲戚们头破血流争吵些什么,不懂村里的年均收入只有五千块意味着什么。
孩子在坟前下跪,周遭念着:
孝子添仓,万石余粮。
只是,当这位孩子长大后不可避免重复父亲的宿命,被卷入洪流,当他背离土地攒下万石余粮,衣锦还乡后又能够给谁添仓?
我们总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抱着刻板印象。
农村等于善良。
而善良,从来只存在于温饱之后。
现实是杓裕村还没有路灯,村民们晚上坐着三轮车出行需要自己打手电筒,因为这辆农用的三轮车并未配备车灯或车灯已坏。
当你只有一个手电筒,你就不会对压死的野狗善良。
农村两兄弟分家,为了公平,一张桌子四条腿拆两半的事情,自古以来不罕见。
一旦扯不清楚,奉上锄头与獠牙。
这就是杜深忠私奔北京不成后,将其牢牢锁住的土地。
别家在干农活时,杜深忠偷摸着拿一本《鲁迅文集》带到苹果地里看,要不就是在家门口的空地上用毛笔沾着水写《道德经》,还能时不时看到他捧着把琵琶拨弄……
农民不种地,不干农活,就是村里的怪人。
没有钱,就要挨老婆的骂,变着花样的骂:
“你是头顶火炭不觉热。”
“鱼找鱼虾找虾,五流子找那蛤大蛤,兵对兵将对将,下三滥才配那恶儿当。”
“有钱的王八坐上席,无钱的君子下流坯。”
这是杜深忠妻子张兆珍常挂在嘴上的一类话。
可是,偏偏别人不关心的事,他最爱咸吃萝卜淡操心。
他残忍到不关心自己,只关心这个世界。
看到城里人把一棵百年古树砍倒,弄到城里去做绿化,他骂着:
“这叫剜大腿上的肉贴脸上,就是看到那点钱了。”
家里的玉米地被獾糟蹋,妻子想要下药把獾毒死,他却说:
“你别看獾吃这点东西,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獾糟蹋点就糟蹋点吧,人都昧着良心卖假种子。”
妻子反驳到:
“獾倒成保护动物了,谁来保护农民?”
杜深忠哑口无言。
他自顾自在劳作间隙敲响锅碗瓢盆的交响曲,关心奥运会,关心神舟飞船发射,不再关心自己农民这个身份。
为了一把690块的琵琶,他和别人合起伙来骗自己的妻子,说只要“400出头”。
这是他心心念念多年的琵琶,在此之前,妻子只允许他拉那把早已走了音的二胡。
他捧着抱回来的琵琶就想捧着刚出生的婴儿:
“终究抱得美人归。”
被妻子“批斗”成下流坯的杜深忠,在这片生长了几十年的土地上是个异乡人。
音乐、文学、书法就是他的毒品,维系着他的生命。
他将自己与这土地的矛盾,与村里人的矛盾,以及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都转化成了和妻子之间的战争,化成了日复日,年复年的争吵。
某一年春节,杜深忠对儿子说:
“你妈妈她不认识我是谁,她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妈妈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要做什么。这就是我最大的一种痛苦。”
他叮嘱儿子一定要好好念大学,一定要走出去。
他如此描述自己的家乡:
“实际上我一开始对这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办法、无奈。”
贫瘠的土地不养穷人。
影片的最后,是村晚的表演舞台。
曲子结束,人群散场,只有杜深忠一个人抱着琵琶呆坐在原地。
人们喊着:
“下来吧!”
他望着这把骗来的,690块的吉他,无言。
杜深忠看透了,他说:
“人有旦夕祸福。”
意思是幸福或者灾难的发生,都不可预料。
因此,最重要的事情只剩下读一本书,弹一个音,写一个字。
朝闻道,夕死可矣。
影片上映十年后的今天,杜深忠70岁了,终日在老屋里写着《九成宫醴泉铭》书法。
他完成了女儿的婚事,培养出大学毕业的儿子。
女儿、儿子贴满了墙的奖状
但他仍说:
自己是个懦夫。
可还要多勇敢,才是勇敢?
原本是时代抛弃了他,却在自身的引力下扭转局面,反过来抛弃了时代。
他执笔写下这样的句子:
“天就是我朋友,地就是我朋友,太阳是我朋友,月亮是我朋友。”
天地间,一片大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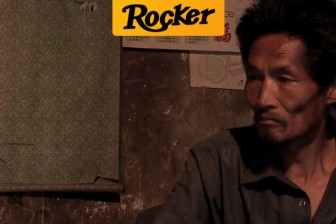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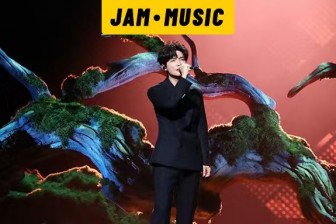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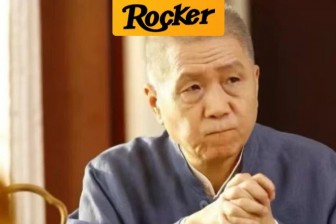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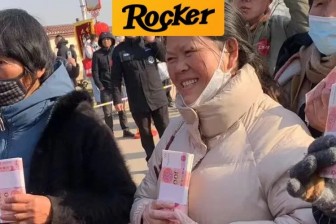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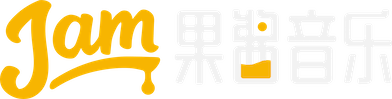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