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离开十年的人又再被提起。
史铁生。
最初是余华说了个段子:“让一个双腿残疾的人去当足球守门员是怎样的体验?”
这个问题史铁生很有资格回答。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期间,作家马原在沈阳工作。他邀请余华、莫言等一行人去沈阳给辽宁文学院的学生讲课,于是大伙把史铁生连着轮椅一起扛上火车。
作家们深夜看了世界杯的比赛,第二天起床后就有了自己是球星的幻觉,在学校篮球上和辽宁文学院的学生踢起了比赛。
双腿残疾坐轮椅的史铁生原本被安排在场边做教练兼啦啦队长,眼看失球太多,余华们只好使出绝招,让史铁生当起了守门员。
“他很有可能一脚被你们踢死”。
史铁生守住球门后,学生们倒是再也不敢射门了,但作家们还是输掉了比赛,因为再也没进球。
其实这趟沈阳之行,原本是马原想带着史铁生去西藏看看。
史铁生说:“下了飞机就有火葬场吗?吓得马原只好请他去了趟沈阳“。
在苏童、西川等老友共同参加的综艺《我在岛屿读书》上,余华说他搬家做过最蠢的事就是把所有信件都烧了,因为有铁生写的信。
大家提起史铁生只是一句平淡的“铁生”,仿佛他不是走了,只是错过了这次老友聚会。
而史铁生的故事由一个个老友补充,最终凑成了一个“人间顽童”的形象。
史铁生21岁就双腿残疾了;
他曾长久考虑要不要自杀;
21岁、29岁、38岁,死神至少找过他3次。
可他回顾这一生却说:我是这个世界最幸运的人。
史铁生大概算最幸运的一批残疾人。
第一辆轮椅是邻居的设计,那个年代连个像样的轮椅都买不到。
父亲捧着图纸满城里找人制作,跑了好多天,才有一家“黑白铁加工部”肯接活儿。用材是两个自行车轮、两个万向轮和废弃的贴窗框。母亲又缝了坐垫和靠背,再搭块木板在前面。
用史铁生的话来说就是,不仅餐桌、书桌有了,连吧台都齐全了。
后来二十位同学和朋友的合资给他换了辆手摇车。
史铁生知道这车其实是二十位母亲的心血:儿女们还都在插队,哪儿来的钱?
这辆车他用了很多年,摇着它去街道工厂干活,去地坛读书。
后来田壮壮要拍毕业作品,想把史铁生的《我们的角落》拍成电视剧。
于是剧组推来一辆崭新的手摇车,想换史铁生手上用旧的,说是更真实。可惜电影拍完又把旧的送了回来,因为那时拍摄经费比不得现在。
收到几笔稿费后,史铁生买了一辆更利远行的电动三轮车,旧的送给了另一个更不容易的残哥们儿。
电动三轮方便出行,也方便把人撂在半道儿。
于是有三位行家自愿做了史铁生的专职维护,甚至一位出国了还专管这事儿。
只要电动三轮机电方面出问题,出国的那位负责在国外找零件,国内的两位负责施工,通过一根海底电缆,配合的无懈可击。
后来史铁生的小说得了奖,要去青岛参加杂志社办的笔会。
朋友便扛着他的手摇轮椅一起上行李车厢,车内密不透风,朋友只好“于谈笑间频频吞服速效救心”。
后来杂志社长看他手摇车抬上抬下不方便,便自言自语道:“有没有更轻便一点的?也许我们能送他一辆。”
最后买来四百九十五块,这可是八三年。据说社长盯着发票不断咂舌。
正是这辆“福”字牌轮椅,开启了史铁生走南闯北的历史。
1996年,史铁生不仅双腿罢工,双肾也怠了工,朋友却一定要带他来美国看看。从大峡谷、大瀑布、大赌城,怕他担心还故意逗趣闻闻他的尿:
“味儿挺大,还能排毒”。
偷袭后史铁生连一般轮椅用着也吃力时,又出来一款电动轮椅。妻子跑了多少趟,从标价三万五砍到两万六。
“就是一分钱不降,我也是要买的”。
在他成为某种励志典型时,史铁生无数次想过死,一连想了几年。
他二十一岁便双腿残疾、坐上了轮椅。
致病原因可能是先天不足、也可能是知青下乡心情憋闷、也可能是乡下条件差不利于养病,总之“活到最狂妄的年龄忽地残废了双腿”。
十九岁第一次被父亲馋着走进病房时,他就下了个决心: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再这样走出来。
二十一岁时又再次入院。
“那天恰是我二十一岁生日的第二天。我对医学对命运都还未及了解,不知道病初在脊髓上将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我舒心地躺下来睡了个好觉。心想:十天,一个月,好吧就算是三个月,然后我就又能是原来的样子了。”
可三个月后他不仅没能出院,病反而更厉害了。
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
他祈求上帝不过是开着一个临时的玩笑,是在他的脊柱里装进了一个良性的瘤子。
“让它是个瘤子,一个善意的瘤子。要么干脆是个恶毒的瘤子,能要命的那一种。”
当病痛超过人的接受度时,“死”便成了个选项。
双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史铁生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于是他摇了轮椅到地坛去。
“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
有时候他在园子里待得太久,母亲会来找,但又不想被儿子发现。只要看见儿子还好好的,母亲就悄然转身回去。
某次母亲又来找,树丛很密,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但这次史铁生决定不喊她。
很久以后听见园中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而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了多少路。
他闭上眼睛想念母亲: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
很久很久,他听见了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在地坛公园他遇见很多人。
有文革时因为说错话被迫靠边站,想通过长跑上报纸换取政治松绑的。可他跑了那么多年,跑第7时报纸登了前6名、跑第3时只登了冠军、终于成了冠军报纸却放了一张大合照。
他还看到漂亮的小姑娘,多年后再遇时已经长大的女孩被一群小流氓围起来欺负,他才发现这姑娘原来是个弱智。
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是不堪说的。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是更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在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残疾30年,他也和死神斗了30年。
两腿初废时,史铁生曾暗下决心:
这辈子就在屋里看书,哪儿也不去了。可等到有一天,家人劝说着把他抬出去。
他吹着风、晒着太阳,又想:摇着轮椅走一走大约也不是什么丑事。
写出点成绩了后,被邀请参加杂志社聚会。
他想起老友的“不要脸精神”:想干事就别太要面子,就算不懂装懂,哥们儿你也得往行家堆里凑。
老友靠着“不要脸精神”在陕北的窑洞里做完了一台台接近医学奇迹的手术。
而史铁生坐着轮椅,开始了一段被老友们扛着走了大半个中国的人生故事。
在五台山“佛母洞”前汽车失控,就要撞下山崖时被一块巨石挡住。他坚持认为这多亏了他轮椅上的那个“福”字。
1980年秋天,因为长期坐轮椅而肾衰初发的史铁生便问大夫:“敝人刑期尚余几何?”
当时大夫说:阁下争取再活十年。
那时没人知道日后会有透析,就像当时的北京才只有三环。
结果他不仅成功活过十年,还坐着轮椅游遍了大江南北。
甚至在被双腿“背叛”几十年后,史铁生坐着电动轮椅,时隔三十年后居然又上了山。
谁能想到我又上了山呢!
谁能相信,是我自己爬上了山的呢!
残疾断绝了他人生的绝大多数可能,但认真考虑死亡后,他也想明白一个问题:
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既然死是一件无需着急去做的事,那么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
腿反正是完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但死神很守信用,试一试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
史铁生去世13年后,余华再回忆他曾写过的信;
信的结尾是: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而这份幸运,只有真正不怕死的人才能赢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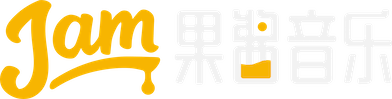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