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西方,音乐节有着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它不仅仅指代着一场户外的音乐盛宴,更是一种文化标志。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举行,被公认为全球音乐节的鼻祖和里程碑,更是流行音乐史中最重要的时刻。这场摇滚盛事远远超出了人们对音乐的理解范畴,而成为西方现代思潮中的一座精神圣殿。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西方人认为,参加音乐节是人生的一个必经过程。
多年之后,西方人理想中的“乌托邦”,在中国得到呼应与延续,2007年国内只有四大音乐节;短短五年过去,国内音乐节数量已经超过了九十个;2013年则大有破百的趋势。音乐节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综合型户外商业活动那般简单,而是一种迎合现代青年需求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手段。国内音乐节的飞速发展,预示着一个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版图正在中国扩张,也折射着现代文化潮流的变迁。
和理想很近,和商业很远
每当音乐节散场,观众一个个井然有序地离开,隐没在人流中。这是摩登天空CEO沈黎晖所有情绪涌上心头的时刻:“我会强烈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因为我,他们走到了一起,在音乐节相遇、分手或复合。音乐节上演了太多故事,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有关于音乐节的独家记忆。”
实际上,沈黎晖的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涵盖中国音乐节的发展历史,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不同音乐节品牌平行发展,熬过不被理解与支持的“地下”时期,终于在某一时刻碰撞出火花。
中国最早的音乐节火种可追溯到1996年,在一座名为开平的小城市,沼泽乐队作为策划人之一发起了以本地摇滚乐队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开平音乐节”。三年后的北京,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则是德国人UdoHoffmann。1999年,由他策划的首届“喜力节拍夏季音乐会”在北京日坛公园举办,“边吃、边喝、边溜达、边听音乐”的生活方式概念,首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
2000年,北京香山脚下,迷笛音乐学校的礼堂内,一场以纯粹摇滚乐为主题,完全免费的学校汇报演出正在展开,那是中国本土音乐节的雏形。“乐队全部免费演出。制作费总共也就两万块钱,包括海报印刷、免费啤酒、音箱租赁,盒饭十块钱一份。”迷笛音乐学校校长、迷笛音乐节创办人张帆回忆道。第二年、第三年,慕名而来的年轻人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演出结束后,观众们围坐在学校草坪上晒太阳。作为一位毫无架子的学校领导,张帆此次出现在演出现场,不是学生的人也习惯亲切地叫他一声“校长”。那些年,“音乐节和理想很近,和商业很远”。
那时的音乐节脱不开“自我陶醉”的标签。乐评人张晓舟曾撰文回忆,2000年的昆明现代音乐节,因为经验与预期不足,各种协调问题频发,最后甚至一度拖欠工资,工作人员消极怠工,本就属“地下”的音乐节变成记者笔下的笑料。靠着热情做事、没有合同、没有专业的管理团队以及没有符合预期的乐迷数量,是这个过程中快速产生又消失的音乐节们共同的特点。
2004年,迷笛音乐节来到北京雕塑公园,门票仅卖十块钱。这是中国音乐节第一次收费尝试。第一次办大型户外音乐节让张帆自己“搭了点钱”,但这次实践迈出了中国音乐节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步。在张帆的努力下,迷笛变成立足北京、辐射全国的文化符号,开始从“小众聚会”向大型商业音乐节转变。
每一年,张帆都为音乐节选择一个关键词:PM2.5,绿色与和平,爱熊行动等等。在张帆看来,音乐节不仅仅是一个聚会,更要直接地表达态度:“报批时,我们不说主题,因为文委只审乐队名单不管主题。”张帆笑说自己是“机会主义者”,大多时候在打擦边球,善于在围剿中找到空子。
2013年,迷笛落户深圳,变成文博会分会场。张帆坐镇深圳大运中心,和记者畅谈与当地知名地产商签订的五年合作计划。在这之前,迷笛音乐节的百度百科还滞留在“所有乐队义务演出”,以至于跟新的合作方打交道,被问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义务的吗,为什么乐队还要出场费?”张帆哈哈大笑,在自信与自傲的背后,却是一套“不死磕”的哲学:和官方以及赞助商打交道,懂得找到平衡点,并坚持摇滚的底线。
“学会妥协,同时要在磨合中让对方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张帆说,有一年,和北京某区政府合作,宣传人员写了一条广播稿让他播放:“我们热爱自然,我们热爱生活,我们反对吸毒,我们友好善良,我们不打架。”这条要求让张帆瞠目结舌,但继而据理力争:“要让他们明白,我们的观众是安全的,经过长久的合作,对方已经从完全不信任,到怀疑,到最终达成默契。这些年,我们的安保数量确实在减少。”

乌托邦里的赌徒
和张帆孤注一掷的开头不同,沈黎晖以更主动、更开放的姿态接纳着各类赞助商和各种不同的音乐形式,过程中赔的赔、赚的赚,磕磕绊绊之下,竟也摸索出了一条运转之路。
同样的时间轴上,沈黎晖也在探索着音乐节的更多可能。1996年,厌倦了走穴生态的沈黎晖创办摩登天空唱片公司。“就是玩票。一个歌手办的公司能有多靠谱?”面对同行的轻慢,沈黎晖很生气,但其实的状况让他无可辩驳:创办的杂志关门,公司剩下两三个人,位于花园桥的办公室一个月3000块租金,沈黎晖每天还琢磨着怎么把楼上租出去,好省下2000块。直到现在,公司还有人耿耿于怀:有一年春节过节,沈黎晖只给了他100块,“但是我自己还没有100块呢”。沈黎晖笑着说。
2004年,沈黎晖绝处逢生。靠着给苹果、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国际品牌做音乐顾问,公司财务状况开始好转。然而,他始终记得2002年时瑞典的Hultsfred音乐节,他亲身体会到音乐节现场的狂欢。除了看大牌乐队表演圆梦之外,沈黎晖还目睹了各种创意市集,包括现场能变出一枚“朋克头”的音乐发廊。2007年,沈黎晖把赚来的钱砸在音乐节上,“血本无归,赔惨了”。但无论是当年办的摩登天空音乐节,还是两年之后的草莓音乐节,沈黎晖都以更主动、更开放的姿态接纳着各类赞助商和各种不同的音乐形式,过程中赔的赔、赚的赚,磕磕绊绊之下,竟也摸索出了一条运转之路。
音乐节正在改变城市人的聆听习惯,人们摘掉耳机,远离录音室音乐,取而代之的是来到现场用音乐社交。曾有一位新加坡的乐迷从迷笛第一届开始就自费“打飞的”追随张帆巡演的步伐;在草莓音乐节现场,促生出一股“街拍”风潮,不止举着维尼小熊、抱着HelloKitty的年轻人成为捕捉对象,李静、高晓松、高圆圆、刘亦菲等明星也逃不过观众的镜头。
大型音乐活动的实际操作,每一天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沈黎晖清楚记得,随着观众增多,在鉴别假票、垃圾处理、厕所摆置、食物供应、场内手机信号乃至观众入口处宽度的测算上,他和团队经历了一次次突发情况。“计划赶不上变化”,第一届草莓音乐节,沈黎晖和工作人员曾眼看一位陌生人将所有工作证“呼啦”一下揽到怀中,拔腿就跑(有证者可免票)。沈黎晖当即傻眼,但很快反应过来,立刻组织团队紧急严查“带证人员”身份,并在入口处补了一天新证。
持续上涨的门票价格、场地费用和制作费用,是中国音乐节进入全面商业运作的明证。而草莓无疑是走在最前沿的引领者。现在的沈黎晖在某些洽谈会上是“成功的商业案例”。对此,他有一丝不被理解的失落。“最早做音乐节的这批人,哪个不是抱着赌徒心态搏击。别人只看到我们现在的门票卖得好,却不懂得为什么我们要花大量人力和物力砸在空白的领域做开拓者。如果只看到音乐节的形式而不理解内涵,就永远不会明白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想做的事。”

星火燎原
北京之外,以丽江雪山音乐节、西湖国际音乐节、热波音乐节为代表的本土音乐节也在各自的城市生根发芽,彼此呼应。2008年,朱建筹办了首届西湖音乐节。第一届主打的是民谣气质。“我们不希望西湖是一个很重型的摇滚音乐节,这跟整个杭州的气质不一样。它的风格应该像杭州一样,有它的坚持,同时不排斥很多东西。”
如今身为《都市快报》副总编的朱建,曾经策划过不少艺术展览和演出,直到开始做西湖音乐节,他才真正遇到了困难:“杭州是旅游城市,这一块带来的经济效益已经足够多,政府不需要音乐节来提供附加值。举办音乐节对政府而言是有一定冒险性的。”
麻烦在审批和操作时相继出现:首先是场地,充满旧时代气质,同时又兼备现代文化活力的西湖最接近朱建对于音乐节场地的设想,但西湖旁边能搭建舞台、容纳大批观众、有一定规模空地的大场地少之又少。第二是治安审批,由于在杭州没有先例,首届音乐节的观众席被要求安置座位,“所有人都必须坐着,音乐节中途不许站起来”。朱建一一照做。但接下来,他和同事们多方试探、沟通,希望在有限的条件中释放出更大的空间。第二年,椅子撤了,人数多了,音乐节气氛越来越好。对此,朱建的经验是:“理想和现实之间,不得不妥协。”
如今,西湖音乐节已经做到第六年。3G门户的老总张向东是朱建的老朋友,从第一届起,几乎每届西湖音乐节他都会来。他不是摇滚青年,但是音乐节的氛围让他感受到自由,文艺给他很多想象和行动的力量。“西湖音乐节的传播半径已经远远突破了纸媒的半径。”朱建说,这几年,外地来的朋友陆续增多。去年,乐评人张晓舟就从北京飞来看混凝土天堂,还有人从东北、北京、上海来到杭州,就为了看一眼黄耀明。
前段时间,赖声川的话剧《如梦之梦》请来李宇春出演,粉丝们把上半场的票全买了,下半场李宇春不演了,粉丝就悉数撤退。这件事给了朱建很深的思考。今年的西湖音乐节,朱建本打算邀请美国歌手罗德里格斯(Rodriguez),无奈七十高龄的他档期排满,无法前来。因为对音乐品质的要求,朱建没请有噱头的明星。最终音乐节请来舌头乐队压轴。“这是我们对音乐的尊重,票房不是我们首要考虑的东西。”
但今年的情况和往年相比有所不同,票房有很明显的增长。这届西湖音乐节最大的特色,是在音乐家风格选择上的多元性,从正当红的选秀明星吴莫愁,到唤醒一代人摇滚正气的舌头乐队;从清新的创作才女戴佩妮,到充满实验色彩的大忘杠乐队;再从独立民谣无冕之王李志,到代表了香港殖民时代流行音乐巅峰品质的达明一派这些不同风格的音乐家亦令现场乐迷呈出鲜明的分化格局,以至音乐节就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如第二天排倒数第二演出的戴佩妮一演完就有她大量的粉丝退场,但同时也有不少压轴的达明一派的乐迷涌入。
从商业上看,音乐家的多元化显然利大于弊,观众流动起来(演出场地设在市中心而非野外令这种流动成为可能)增加了总票房;这一策略也提升了音乐节本身的质量,显得更宽容,海纳百川般为更多层别的观众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提供了可能。
虽然今年的票房不错,但朱建更希望相对平缓稳定的发展。“我们不想借助政府的影响力,也不希望有一天突然有一个发展的指标和要求,这也会超出我们的能力。”面对迷笛和草莓等音乐节品牌的扩张,朱建却表现得很轻松:“我们没有产业化的基础,你硬要让我们产业化,也没有条件。”朱建认为,中国音乐节的市场有很大的空间与可能性,正好可以用西湖这类音乐节去探索。“我们尊重其他音乐节,但我们不会简单复制。西湖音乐节真正的价值,首先是源于服务,驱动力来自公共需求,而不是产业和政府的驱动;其次,是作为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存在。商业是规范并保障我们行动的一种必要手段,但不是首要目的。”

抱团生存
2009年开始,草莓、迷笛两大音乐节在北京成熟之后,选择向外突围,做不同期的全国巡回性演出。今年是迷笛音乐学校二十岁生日,迷笛音乐节的足迹已走过了北京、镇江、上海、日照、贵阳、深圳等地。摩登天空今年也迎来其十六岁生日,草莓音乐节也走过了北京、镇江、上海、武汉、西安等地。2011年,两个音乐节在镇江第一次交锋,拉起了音乐节之间同地竞争的序幕。
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让在一线城市之外的乐迷渴望音乐节在本地落地。同时,扩张也意味着主办方自身能更长久地生存。张帆这样看待巡演的必要性:“德国的音乐节,光夏天就有上百个。澳大利亚thebigdayout音乐节,在珀斯、布里斯班、悉尼、墨尔本、黄金海岸五地做巡回。中国的国土面积很大,巡回音乐节能满足各地的青年。中国的音乐节市场没有饱和。巡回是个特别合理的事情。”而沈黎晖也认为,巡回音乐节登陆,和本土品牌在不同档期打擂是一件双赢的事:“有经验的音乐节去新的城市,可以帮助更快培育出一个听众环境。在与本土音乐节品牌一起发力的同时,别人在帮助我们开辟市场,我们也在帮他们开辟市场,甚至帮助本地的音乐节,抱团生存是这个阶段最合适的发展模式。”
向外的扩张必然会和政府发生关系。在多年和政府打交道的经验中,张帆、沈黎晖二人锻炼出了“不卑不亢”的姿态。张帆说,粉丝群的力量是和政府进行沟通和对话的后盾。2007年开始,迷笛拿到了全国第一笔政府支持音乐节的资金:海淀区委宣传部的50万的文化创意产业扶持资金,2010年则继续得到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文化创意产业扶持资金。而在迷笛贵阳、日照、镇江站也都是有政府色彩和背景,“我们在北京上海其实可以不靠政府,但在二线城市,音乐节市场不健全,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来支持这种运作。当对方支持的资金可以基本涵盖掉一场的大部分成本,你才存在盈利的可能”。
沈黎晖不太敢拿政府的钱:“有时候,政府的钱没有持续力.如果拿政府的钱,我们宁可去做承办工作而不一定要做草莓的品牌,那样太耗时耗力。武汉站是规模最小的草莓音乐节,我们不急于做大,而是一点点培养,慢慢成长。这一点可能不太符合商业准则,但我们更注重长期,看一个事儿最少看五年。”沈黎晖尝试了台湾、西安舞台,收购了西安张冠李戴音乐节,并尝试在西安等地设立分公司,挖掘本土艺人。“要改变一个城市的音乐趣味乃至生活趣味,不是做完音乐节拍屁股走人就行,而是要扎根当地,对当地的独立原创音乐有贡献。”
孙孟晋则认为,各地政府都不一样。“有些政府考虑的更多是政绩,而不是单纯把这它当做一个文化项目来看。也许换届,这种合作和扶持就没有了,我希望有一个持续的、健康的、长久的东西。”他举了个例子,在某些地方,安保变成政府赚钱的工具。“警察会要加班费,我要来100个警察帮你保护,但是你最后看到在现场就那两辆警车,这方面政府应该维护自己形象和口碑。”
2013年,迷笛和草莓音乐节都实现了总体上的盈利,其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门票与赞助收入即能维持良性运转。与此同时,另一种不收门票、更多依托于政府和赞助商的音乐节模式正在悄然靠近。“你可以想象一下,利用3D呈像技术,20米高的大猩猩和熊代替DJ打碟,配上电子乐,激光字在眼前乱飞。这套技术我们可以轻松拷贝30场,到时根本不用请大牌艺人,就可以让观众嗨翻天。”前华纳唱片公司总裁许晓峰坐在自己的深圳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展示厅里向记者解说。

未来的音乐节
“音乐节是赚钱的生意吗?”这是每一个徘徊在大门前跃跃欲试的尝鲜者要问的问题,然而,张帆却给提问人泼了一瓢冷水,“全国100个音乐节,赔钱的可能有97个。大家表面上看觉得音乐节挺热闹的,其实音乐节就像个无底洞。所以,这个行业吸引不到风投,因为战线太漫长,投资回报率也小得很。”沈黎晖甚至会开玩笑劝说专业投资人对自己“敬而远之”,他表示,账面上的盈利,基本被他用作第二年的制作费用,而制作费和场地租金的上涨,使盈利、投入变成一个乐此不疲的循环。
对音乐节内容的批评不绝于耳。许晓峰表示,中国音乐节市场的繁荣,最大反哺对象是摇滚乐队,然而,这类艺人的发展程度却远跟不上音乐节数量的增长,于是,雷同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迷笛愿意做任何音乐节的顾问,”张帆坦言,“我们不怕雷同。微博上曾有乐迷说,从迷笛舞台上出名的乐手,在绝大部分小型音乐节上表演只像蹭饭,在迷笛才能收获到山呼海啸的互动和真正的尊重。”短期经济效应促生出许多只有一届的音乐节,许晓峰就曾遇到谈到最后一步,却突然因赞助商撤资而取消的音乐节。但沈黎晖觉得,应该对这类不成熟的音乐节多点包容。“至少音乐节养活了一批乐手,乐手能靠演出生存,才有为音乐节输血的可能。所有音乐节都干了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就是让人们走出家门,意识到真刀实枪的现场音乐和晚会对嘴、MP3有什么区别。”
日本最大的摇滚音乐节FujiRock现场,散场后的场地一片垃圾都没有,不止如此,大部分国外音乐节只有一两辆警车,几位警察维持现场秩序。许晓峰说,中国的音乐节在一两年之内无法在秩序和规范管理方面达到国际水平,而政府的信任度、报批流程的简化,无疑会节省很大一部分沟通成本。
张帆强调,专业化管理确实是音乐节口碑与盈利并举的保障。“这个行业妄图走捷径的人最终都无法生存。”丹麦的Roskilde音乐节由同名基金会负责日常运营,基金会得到政府的部分支持,同时又把每年的票房收入拿出一部分来做公益事业。而像苏格兰的爱丁堡艺术节,下设七个分项,由爱丁堡政府支持,由一个董事会和一个高层董事会来运营,每年,参与董事会的7个艺术节主席、市政府代表等会研究次年的投资、发展计划等。这两种管理都很科学,公司形式具备很清晰的财务管理、人事管理,还有细致长期的规划和目标定位。而2005年开始,迷笛注册演出公司,2006年投入音乐节运营,后来还取得国际艺人的经纪资质,都代表了张帆的专业化努力。
音乐节的人情味也必不可少,张帆表示:“音乐节应该是一个节日,观众来了以后要像过节一样。1975年,我上小学。那时候的物质条件非常匮乏,只有过春节的时候,每家每户才能分到一条仅有的带鱼,一包花生瓜子,给小孩儿一把糖豆儿。但是,我们觉得特别快乐,因为那是节日。所以我总觉得,节日是跟钱是无关的,音乐节同样也跟钱无关,不是说你要到大投资,就能够做一个特好的节日。人们在一定的场所里,保持愉快的心情,感到幸福放松,并彼此获得温暖。我觉得这就是节日。”
在沈黎晖看来,与时俱进也是音乐节能够传承的重要条件。发端于改革开放浪潮之初的中国音乐节,并未经历上世纪六十年代“枪炮与玫瑰”的洗礼。在中国,反叛和抗争早已不是音乐节需要表达的主题,闻名遐迩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一个可以致敬但永远无法复制的过去。和偶像乔布斯一样,沈黎晖的操办核心是推陈出新,做“未来”的音乐节,今年他尝试把音乐节和互联网社交网络联动,在创新中寻找新的乐趣,和陌陌合作的“搭讪广场”应运而生。
第一年最赔钱的摩登天空音乐节,反而是沈黎晖最有成就感的。在音乐节开始的前一晚,沈黎晖难以入眠:“所有邀请来的大牌已经都在酒店了,场地准备好了,音响准备好了,这一切就要发生了,而我就在这里。”每次散场时,沈黎晖坐在舞台边看工人拆台,“一个小时后再去看,哎,就这么消失了”,保洁工人迅速清理着场内遗留的垃圾。沈黎晖内心有种超现实的感觉,“音乐节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创作。就像行为艺术一样,你创作了一个事物,大家来参与,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这也是一种满足。音乐节结束的时候特别累,第二天早上醒来,喝一杯咖啡,阳光照射进来,你会觉得哇,生活真不错。对,那感觉也是很美妙的。”
沈黎晖、张帆、许晓峰都曾担任歌手或乐队主唱。正是这批60、70年代出生的人,带着“最后”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对音乐纯粹的热爱,全身心投入这项事业。大学时期念国际贸易专业的张帆,在学校一直是个热衷文学、曾组乐队担任主唱“不务正业”的学生,但正是这点儿爱好让他最终走上了音乐道路。如今,关于音乐节具体的工作,全都交由专业团队打理了,而张帆则更能以普通观众身份,在舞台下享受每场演出。闲聊间,张帆透露,等自己退休的那一天,会集结原乐队成员,在自己搭造的舞台,献上一曲昨日之歌,作为完美的落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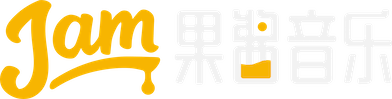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