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家意大利风情的小咖啡馆里,谢天笑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手里夹着一支烟,头发已经长到肩膀那么长,用个黑卡子一类的东西往后别着,但他打理的不太好,有两缕头发始终支楞在外面。起初我以为他是不在乎而胡乱弄的,后来才知道,大概还是自己没注意,因为当采访结束合照时,老谢(即谢天笑,下同)看着自己的形象抱怨道:“我怎么那样儿?看着那么脏啊。”
在他唯一参与的一部电影《盗版猫》里,谢天笑有两句有意思的台词:“你成天光喜欢吃肉,你当然不长头发了。你看我,我成天吃韭菜,我吃韭菜我这头发长的多好。……你看你那个熊样。现在都流行吃素你知道不,这是科学家说的。你看我这身材,多国际化。”
此刻在这家咖啡馆里,老谢没带墨镜,与台上那个能轻而易举就让台下为之沸腾的他截然不同。身边的朋友是老谢的铁杆粉丝,笑着看得他发毛。姑娘说,“老谢,我特别喜欢你!我真的太激动了!”老谢两条胳膊并在一起,双手合十夹在两腿之间,抬头看了一眼姑娘,又有点儿腼腆似的低下头,抖两下肩膀,说:“你激动,我都激动了。”
老谢不是客套,他的激动呼之欲出,写在脸上。上一次“激动”是我们的访谈间,他向服务员要了一包烟,人家说我们这里不卖烟。然而转过身拿了半包中南海递给他,说,“今天您运气好,刚那桌客人留下的,不介意就给您。”“呦!呦!有点儿意思!”老谢接过烟,拿出一根儿边点边嗞嗞地咂嘴,像是在自己佩服自己的好运气。
除了这些,如果你看过他朋友圈里那只得意的、五指努力分开的脚丫子自拍照,或许你会更赞同我的想法——《盗版猫》里那个坐板儿车、跟着音乐跳舞的角色是他在本色演出,是谢天笑不带吉他不唱歌时的另一面。

1991年,谢天笑18岁,他违背了家里的意愿,没有成为一个在党政机关里画黑板报的宣传员,而是一个人来到了北京,住在圆明园边儿上。这个从小被京剧与国画熏陶出来的家伙在那时候刚刚踏上音乐创作之路不久。当年,还很难从与一票先锋画家共为邻居的谢天笑身上看出什么关于日后“摇滚新教父”的端倪,那时候的他还在不住地感叹身边艺术家们的作品:“他们能把一些正义、严肃的东西或人画的特别邪恶,以前我都没见过那样的画,他们都特别叛逆。”
现在的谢天笑,古筝与吉他成为一个标志。崔健在看谢天笑古筝与吉他完美对谈的表演时,曾说那一刻让他“激动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即便没怎么听过谢天笑的摇滚,或者还叫不上他名字的人,在看到他的演出时也会说:“嘿!是那哥们儿,他唱着唱着摇滚,还能中间给你来段古筝。”
谢天笑的歌迷说他即便是玩雷鬼也不是牙买加范儿,他的音乐,始终是自己的范儿。
传统乐器与摇滚这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东西,在谢天笑手里完成了完美的融合。在谢天笑看来,如果中国摇滚乐做得和美国摇滚一样,那就不用再做了。“在美国那段时间,由于无聊,看了很多中国的书,后来我发现有太多值得传承和学习的东西了,过去我都没有发现。我觉得自己作为中国人很幸运,因为有很多东西可以利用。比如自己的文化背景。有很多很多非常有意思、非常深奥的东西,可以学习和研究,可以和自己的艺术结合在一起。做艺术应该有自己的特点,作为中国人来说,我的特点是从中国文化中寻找出来的。”
我问他这种结合是否源于小时候工笔画、国画以及京剧这些传统中国艺术对他的影响。他想了想,似乎也很难找出儿时与当下的某种关联,想来想去,得出来的一点总结还是画画本身无关,而是也蕴含着一股反叛精神——“可能就是当年画画老师的那句话吧,‘百分之百的临摹,还不如百分之一的创造’。”那京剧呢?“我觉得挺无聊的。你不可否认他是很牛的一个东西,非常辉煌的一个艺术门类,但那不是我的表达方式,我不喜欢。”

去年,和摩登天空的三年合约到期,谢天笑选择了单干。身边的经纪人兼宣传,是他简单的团队组合。老谢强调,和摩登的合作没有问题,他们还会有别的合作。但自己是个懒惰的人,这样一来,在“音乐创作上以及其他的时间安排上,我能有更大的空间。”
老谢把音乐创作上的灵感称为“神来之笔”,他不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也不是勤勤恳恳的学院派。他从不会像一些音乐人一样要求自己一定下周二之前交出一首歌。他喜欢玩,喜欢睡觉,喜欢游泳,喜欢在自然状态下享受音乐带给自己的快感。
“有的人说,天笑你做了这么多年的音乐,你坚持到现在真不容易啊。我没有觉得我在坚持,我觉得做音乐应该享受它,你享受这个过程才能做出好的东西。如果是坚持,那太累了吧。”
舞台上的谢天笑,总是唱很多,话很少。他曾拿“谢三克”作为调侃,也曾操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略显老土的问候方式与台下互动——“你们好吗?我们好久没见了吧。”——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了观众的热情。往往可以看到,老谢一上场,他还在冷静的调试吉他,台下已经沸腾。他说与不说都不重要,他发生什么也不重要,来到这里,只冲他的摇滚乐。
舞台下,老谢说他非常非常爱他的妻子。他还喜欢做饭,他的炸酱面做的不错,但不喜欢洗碗。当我们聊了不久,我对老谢说他和我想象的太不一样。老谢有点儿惊讶,“是吗?那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告诉他我脑海中的固有模块,老谢说:“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媒体和老百姓,对中国摇滚乐有一些误读,有一些妖魔化。总觉得摇滚乐特别……喝酒啊、毒品啊,乱啊,但是别的行业也有这样的人啊。流行音乐里面可能更多呢。还是分人吧,我觉得。”
从18岁聊到到41岁,老谢用“我操”表达了对时间流逝的感慨。他说他喜欢现在的自己,“就是想好好的做音乐,好好的生活。”而当谈到那些过往,老谢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坚定。他说“摇滚乐改变我的命运和我的生活,给了我现在的一切,我要把我的一切还给摇滚乐。”

《旅伴》: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你?
谢天笑:可能是我写的歌简单、好听……或者因为歌词吧。
《旅伴》:你有一个头衔是“摇滚乐现场之父”,你认为是哪些因素让你的现场更火爆?
谢天笑:其实我演出的时候很少能顾及到台下。我认为最好的、最完美的演出,恰恰是忘掉自己在演出,因为只有在舞台上忘掉自己,别人才能记住你。我通常认为自己好的演出就是自己满意。我不是那种对自己要求特别高的人。有的人要求特别高,总认为自己每次演出都不是最完美的。而我对自己的演出评价只有“糟糕”和“好”两种状态,特别极端。“还行”也有,比如工体那场演出我觉得还行。
《旅伴》:那场有什么问题?
谢天笑:我有点儿紧张,都是人嘛,对吧。其实我演出也特别多,不应该紧张,但我还是有点儿,刚上去的时候状态没把握好。
《旅伴》:是那个场地让你紧张了吗?
谢天笑:因为所有人给我的那个信心,我感觉我上工体了,有那种心理压力。
《旅伴》:工体对你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
谢天笑:它是一个台阶,让我开始一个新的阶段。我上去以后,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儿紧,不过几首歌后状态就调整过来了。
《旅伴》:提到摇滚,人们会有一些固有的印象标签,比如歇斯底里,比如长头发。在你的表演中,每一次高潮来临都是发自内心的不由自主,还是会有设计的成分?
谢天笑:当然是发自肺腑的。我很少故意设计什么,一般演出都比较随性。如果是设计好的,我反而会掌控不好。有人会设计的,我认为,一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样设计的人还是知道什么样的音乐是比较深厚的东西,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至少他会标榜自己是摇滚乐,他还是有他的欣赏能力吧。
《旅伴》:摇滚乐是好的东西,这相对什么来说?
谢天笑:流行音乐吧。
《旅伴》:流行音乐怎么不好了?
谢天笑:也没有不好,有的流行音乐也很好听。但我觉得流行音乐首先是商品,为了迎合。而摇滚乐最重要的是它有反叛的精神,有反叛才会有发展。我其实也很喜欢有的流行歌曲,不过我通常听的都是比较老一些的。不过最近我们出去喝酒,经常听一些蕾哈娜。

《旅伴》:摇滚乐的听众也越来越多,大众的接受度越来越广,更多的流行歌手也在自己的歌曲里加入摇滚元素。也许有一天你的音乐也会成为主流。
谢天笑:我觉得那样我会很高兴。我依然希望能够赢得主流的……
《旅伴》:承认?
谢天笑:不是。是……认可。
《旅伴》:如果成为主流,你必然会面对更多的框架,你可能需要做很多妥协。
谢天笑:对,所以以我的性格,我注定没办法成为一个主流的艺人。我是一个地下的艺人。
《旅伴》:当你被更多人接受,你会面临表达困难吗?
谢天笑:我觉得我还没有。我说心里话,我觉得我做的事儿太少了,浪费的太多了,原来玩的太多了。我真正想做的音乐可能刚开始吧。
《旅伴》:走到现在为止,妥协过吗?
谢天笑:妥协过。
《旅伴》:比如?
谢天笑:比如以前一些为了宣传的事会妥协。以前为了宣传去一个电视台录节目,玩扎气球、猜谜语的游戏。我觉得我把人那节目弄的特别糟糕。我觉得我也不适合这种节目,首先我自己不喜欢,再一个我会营造那种娱乐的感觉,有时候还会冷场。我想主持人可能也会很反感我这种人吧。然后回去我就特别埋怨自己,特别不接受自己。
《旅伴》:音乐本身有妥协过吗?
谢天笑:实际上也会有。比如以前制作一张唱片的时候,制作人跟我说这首歌我们一定要分轨录,品质会更好。但是我不认为,我就喜欢同期的那种。但同样一首歌,品质好可能接触的人会更多。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品质不是最重要的,我更在意一个乐队作为一个整体的那个感觉和状态。但我最后还是会接受分轨录的方式。
《旅伴》:你喜欢团队作战?
谢天笑:对。
《旅伴》:那当初为什么要单飞?
谢天笑:乐队只是一个阶段。我那时候也年龄小,觉得玩摇滚一定是一个乐队,我应该是主唱。后来我觉得其实也不重要吧,那只是一个名字而已,实际上那时候的创作和现在的方式差不多。
《旅伴》:你享受站在中心被更多人接受?
谢天笑:那当然。
《旅伴》:你认为现在还有那种纯纯为了艺术而存在的音乐人吗?
谢天笑:一定有。实际上现在还有很多地下乐队是真正在做音乐。
《旅伴》:你不是?
谢天笑:我一部分是,但我不太是。
《旅伴》:以在你现在这个年龄,会越来越理性地看待摇滚吗?
谢天笑:创作音乐的时候不会,后面的事情……比如宣传这些,我不太懂。
《旅伴》:现在摇滚对你来说,更多的是一份职业,还是一份追求?
谢天笑:摇滚对我来说是一切、全部。我接触到摇滚乐之后,它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我的命运。我开始做摇滚之后,我才找到一个适合表达自我的工具。我觉得如果现在我不玩摇滚乐的话,我也应该不是朝九晚五的那种人,我应该是另外一种人,可能不会是个好人吧。
《旅伴》:如果不做音乐可能做什么?
谢天笑:黑社会吧?
《旅伴》:老大还是马仔?
谢天笑:慢慢会混成老大的(笑)。
本文转载自《旅伴》杂志,意在传递更多信息,并无任何商业目的。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请作者尽快与本站联系,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删除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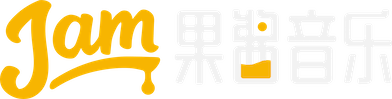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