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作家Jonathan Campbell两年前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摇滚的英文著作《Red Rock:The Long Strange March of Chinese Rock&Roll》,RedRock其实也可以翻译成“红岩”,正如在书的内文中,作者将直接用拼音来命名Chinese Rock&Roll——“yaogun”,以强调摇滚乐在中国的特殊语境和复杂属性。“Red Rock”这个词虽有过于强调意识形态语境之嫌,但也不无道理,尤其是用来描述和分析早期中国摇滚的时候。
但Red Rock如今也在转化为pink rock,中国,早已进入一个粉红色的时代,意识形态对抗的红色时代,早已经转化为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杂交混合而成的粉红色时代。把摇滚乐神圣化的“红色摇滚”情结似乎变得有些不合时宜。一方面,从崔健开始,“摇滚乐”一直被与“流行音乐”划分开来,甚至有时候被当做某种对立的范畴,而另一方面,摇滚乐越来越普及和流行,理所当然地归属于流行音乐的范畴。
过度的神化,以及贴抽象的概念标签,都是没有必要的。比如《城市画报》新一期封面是汪峰,标题是“汪峰:现在最摇滚”。但当汪峰自认为最摇滚而有些人认为他不摇滚甚至是伪摇滚,“摇滚”这个标签就变得很无聊了。“摇滚”这个中国译名和音,确实有一股大蒜伴辣椒的呛人味儿,漱口水一下去,你还想再接着狂吃,对于摇滚二字的捍卫,无非是张扬摇滚精神——不只是形式——而所谓“摇滚精神”,无非是被当做“反叛精神”的音乐同义词。但在一个疯狂的消费主义社会,任何词都会被滥用——就像“朋克”已变成发廊的名字——都会变成白开水,甚至自来水。
中国摇滚的精神属性依旧有赖于残存的意识形态压制,至少对cctv来说摇滚依旧是敏感词。但近年地方台的春晚,以及选秀节目已经争先恐后地摇滚了,摇滚乐先是作为青少年亚文化越来越得到普及,再是突破主流文化的保守堡垒——电视——而得到更大传播,但消费娱乐文化也势所难免地对其进行了过滤、软化乃至消毒,于是,“摇滚”这个词势必渐渐却除其原有的倾向性乃至火药味,而越来越接近于中性。这也正是为什么当选秀节目中有人玩摇滚,一方面容易赢得喝彩,另一方面也容易被讥讽为“娘炮”——很多铁杆滚友还是容易将摇滚当成理想主义圣斗士,将摇滚和选秀娱乐对立起来。
但中国摇滚恰恰是从选秀开始的,崔教父曾经也是个“超男”或“快男”。在1986年5月以《一无所有》而揭开中国摇滚序幕之前,其实崔健和他的战友曾经两度参加歌唱大赛,竭力寻找表现自己的机会。第一次他是和王迪、刘元、黄小茂一起去的,演了两首歌:《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评委有王昆、李双江,第一轮就给刷下来了。第二次唱的是《假行僧》,有所进步,第二轮才刷下来。教父原来也曾是快男,听上去好像很不那么摇滚,但是首先,当年别说摇滚乐,连普通流行歌曲和“轻音乐”都一不留神被当做“精神污染”,另外,除非去公园跟唱京剧跳秧歌的老头老太抢地盘,崔健他们差不多没什么像样的公共空间(比如剧场、酒吧)可以去表演。

问题不在于摇滚还是不摇滚,也不在于选秀节目这个平台和媒介,而在于音乐好不好,精气神牛不牛逼。
有一天晚上微博上挺吓人,好多老炮在呼天抢地涕泗横流,有的大v甚至在感谢汪峰导师令“摇滚不死!”,一看原来是有人在《中国好声音》翻唱《hey jude》(钟伟强,毕夏),还有人翻唱《一块红布》。
又有人翻出那部日本NHK的纪录片《hey jude与捷克自由的故事》,那部片子说的是女歌手玛尔塔·库碧索娃在“布拉格之春”年代将《hey jude》重新填词,激励捷克“六八一代”为自由而战的故事。王晓渔在微博里故意把这部片子说成《捷克好声音》。
但显然,在中国好声音做个k歌之王足矣,要那么多故事干嘛?中国好声音也好,汪峰导师也好,跟摇滚的死活又有何干?
刘彩星和高扬在中国好声音上翻唱的《一块红布》,更是让我一个老友在微博上号称“泪奔”。当然,这首歌在二十几年前也曾经令我泪奔,令王朔泪奔(详见《我是王朔》一书自述),令无数人泪奔。然而崔健唱一块红布你泪奔,中国好声音唱一块红布你也泪奔,这泪点是不是跟尿点快有一拼了?
经典就是用来不断翻唱的,崔健早已被翻唱过无数次,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只有两个,一个是夜叉乐队的金属版《像一把刀子》,收录在一张翻唱崔健的合辑《谁是崔健?》中;另一个是2004年12月31日在广州的一个新年音乐节上,崔健和王磊领导的泵乐队合作,以泵乐队的dub reggae方式翻新了《不是我不明白》和《从头再来》,只此一次。
《一无所有》被翻唱得最多,胡德夫曾经跟我说当年他也翻唱过《一无所有》,可惜无缘听到;张惠妹在北京演唱会上的版本也不坏,有她独到的劲儿。至于梁博,对他来说翻唱《一无所有》和翻唱《我爱你中国》,本质上似乎没有差别。
 (图注:华晨宇翻唱崔健《假行僧》)
(图注:华晨宇翻唱崔健《假行僧》)
问题不在于翻得有没有新意,而在于是否动人,刘彩星的新意是以田震的方式翻唱崔健,但是田震和崔健的区别,就不必多说了吧。
去年有一次,微博毒舌女神叶三深夜发了一条微博:“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粉丝汹涌而至,纷纷转发并唏嘘不已,都当是三爷例牌的深夜发骚。
过后不久,我在广州方所书店做讲座,念了这一条微博,问是否有人知道出处。没人知道。在杭州晓风书屋,我又抛出这一条,还是没人知道。《一块红布》最后这句令朔爷舟爷三爷等等无数爷们痛哭流涕的歌词,如今已沦为一句湿漉漉黏糊糊的小清新情话。一块红布,早已沦为一块粉红的布。
刘彩星唱至少还唱出了一股泥土气息,而被粉丝称为“花花”的快男冠军华晨宇唱的《假行僧》就是从头到脚一股子香水味儿。《假行僧》不幸被从侠客的大地一把拉进了娘炮的闺房,你不能说这哥们唱的太矫揉造作,因为矫揉造作就是他们的天性——所谓做作的很自然,他也是真诚的,能把假行僧唱成真行僧。但比起张信哲的《假行僧》,华晨宇好像还强一点;比起一个叫泡泡糖的乐队,刘彩星高扬的《一块红布》还算节制,这“泡泡糖”是把“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弄成“我要永远这样陪伴着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嗨皮”了。
你也不能说这就不是摇滚这就是伪摇滚。当摇滚越来越流行越来越泛滥,或许你可以像Jonathan Campbell那样,将Rock&Roll说成“yaogun”,以继续强调其理想主义血性和意识形态文化独特性,或者像我在九十年代一样,将之说成“肉啃肉”,稍嫌粗俗地强调其原始野性和活力,甚至像盘古乐队那样——去年他们有一首歌名为《咬滚》——“咬滚”似乎已不齿于摇滚,它要狠狠咬摇滚一口。
2006年,我在深圳某体育馆策划了一个大型音乐会。主办方演出前特意提醒:希望崔健不要唱那些歌名有“红”字的歌儿。
审查标准因地因时而易,比如去年年底崔健五棵松音乐会,《红旗下的蛋》就不能演,但《一块红布》却可以。崔健双眼蒙着一块红布吹小号这一形象,早已成为那个风云激荡的启蒙时代的一大启示录图景,2011年年初,在工体的崔健摇滚交响音乐会上,演到《一块红布》时,一块巨大的红布徐徐落下,把整个舞台遮住。
那一块红布又徐徐收起。而时代的大幕,如今已换成一块粉红的布,把我们通通遮住。
20号晚汪峰成都演唱会,当汪峰一路《飞得更高》高歌《我爱你中国》,观众也跟着高呼章子怡。成都人是多么幽默,多么摇滚。
当时代从李双江进化到李天一,让我们重温一下1985年崔健选秀的魔幻场景:他对着红歌天王李双江,怒唱《最后的抱怨》——那可是崔健最出色的的歌之一,尤其在后来录音之后:
记得那一天,我的心并不纯洁
我迎着风向前,胸中充满了抱怨
我不知何时被伤害,可这伤害给我感觉
我不是在回忆,我也不想再回忆
可那不明白的过去,使这风显得更加强烈
那不坚定的意志,使这伤痛更加厉害
我心中只有爱情,可爱情它不能保护我
Oh Yeah 我只能相信我自己,
还是在那一天,我要发泄我所有的感觉
我迎着风向前,不怕越走越远
我不知到底为什么愤怒,可这愤怒给我感觉
我不是在回忆,我也不想再回忆
可那多少年的风,总是变换地吹个不停
把多少人的伤害,吹成了一次次革命
我心中只有爱情,可爱情它不能保护我
Oh Yeah 我只能依靠我自己,
我要寻找那愤怒的根源,那我只能迎着风向前
我要发泄我所有的感觉,那我只能迎着风向前
我要用希望代替仇恨和伤害,那我只能迎着风向前
我要结束这最后的抱怨,那我只能迎着风向前
向前向向前,我迎着风向前
向前向向前,我迎着风向前。
——来源:腾讯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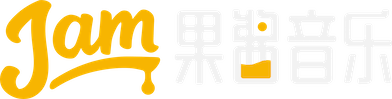

评论